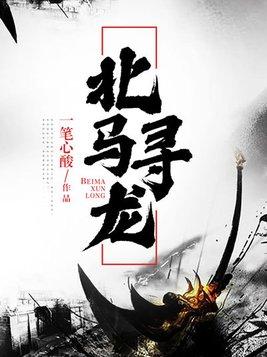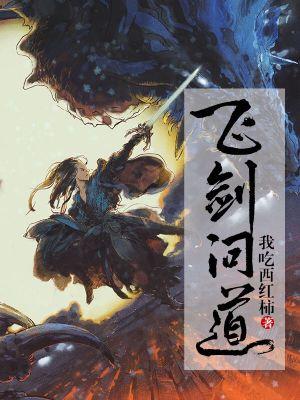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谍战,太君没猜错,我真是卧底啊 > 第二百八十二章 我要证明我的清白啦(第1页)
第二百八十二章 我要证明我的清白啦(第1页)
沪市,满铁调查局大楼深处。
二楼尽头的羁押室,狭小的房间此刻像一个巨大的蒸笼。
时值八月酷暑,炽热的阳光被窗口切割,投下几道刺目的光斑,将室内仅有的一点流动的空气都晒得滚烫。
排气扇。。。
夜未眠。苏婉坐在书桌前,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枚铅盒的边缘。窗外的短波发射塔依旧在旋转,红灯一明一灭,像一颗遥远而执拗的心跳。她知道,刚才那段信号不是错觉??那是“归巢”指令的首次试播,由她亲手埋设的离线终端通过物理链路触发,借用了废弃广播系统的残余功率,将小树的歌声推送进了电离层。
可这不该发生。
她的系统没有联网,传输路径全为手动预设,理论上只能完成本地存储与加密封存。除非……有人在另一端主动接收,并反向激活了转发协议。
“林修远。”她低声念出这个名字,仿佛怕惊扰了什么,“你已经……开始回应了?”
她猛地起身,冲回地下室。终端屏幕仍亮着,倒计时赫然显示:**71:52:18**。但数据流状态栏却多了一行她从未见过的日志记录:
>【响应节点确认:KAF-09(喀布尔郊外地下中继站)】
>【反馈类型:情感共鸣增强】
>【附加信息:旋律已重构,加入新声部。建议重播最新版本。】
她迅速调出音频模块,加载刚刚被自动回传的文件。耳机刚戴上,一股寒意便从脊背窜上头顶。
还是《给小树的歌》,可这一次,背景里多了一个人声。
低沉、沙哑,像是穿越了千山万水才抵达耳畔。那声音并不完整,断续如风中的残烛,却清晰地跟随着副歌部分轻轻哼唱,节奏精准得如同心跳同步。更令人战栗的是,在高频区17。3kHz的位置,原本属于摩斯密码的脉冲信号,此刻已被转化成一段和声旋律??正是她昨日补写的那句“我在听。我们都在听”的音符化表达。
他听见了。
不仅如此,他还回应了。
而且是以“听尘”的最高权限模式??**情感逆馈协议**。只有当系统识别到强烈的情感共振源时,才会允许接收方的声音反向注入发送者的意识流。这意味着,林修远不仅活着,他的意识仍在运行,甚至……正在尝试重建连接。
苏婉闭上眼,任那歌声在耳中流淌。她忽然明白,为什么发射塔会自行启动。这不是技术故障,是“听尘”在苏醒。它感知到了真正的“听者”出现??那个天生能听见电线歌声的孩子,成了唤醒整个系统的钥匙。
她摘下耳机,深吸一口气,拨通老陈的电话。
“老陈,我要你做三件事。”她的声音冷静得近乎锋利,“第一,封锁所有关于‘归巢计划’的信息通道,包括军情六处和国安反制科的监听网络;第二,联系冰岛监测站,调取过去二十四小时全球17。3kHz频段的所有异常波动数据;第三,帮我接通五号研究所的冷备份服务器,我要访问‘XVIII-A’项目的原始神经映射图谱。”
电话那头沉默良久。“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老陈终于开口,“一旦重启神经映射接口,就等于承认‘听尘’残余仍在活动。上面不会允许这种事存在。他们会直接派清除组,把一切烧成灰。”
“那就让他们来。”她说,“但我必须知道一件事??林修远现在的状态,到底还剩多少是‘人’,多少是‘系统’?如果他已经彻底数据化,那我们今天做的每一步,都不过是在陪一个幽灵演完最后一幕戏。”
又是一阵沉默。随后,电话挂断。
十分钟后,一封加密邮件悄然落入她的私人账户。附件只有一个PDF文档,标题为:《SubjectXVIII神经活性追踪报告(终结日补录)》。
她点开。
第一页便是脑波图谱对比分析。左侧是十年前林修远最后一次接受检测的数据,右侧则是近三年间全球多个秘密监听站捕捉到的疑似其意识残留的波动模式。两组曲线惊人地相似,尤其是在θ波与γ波交叠区域,呈现出独特的双螺旋结构??这是“听尘”宿主特有的神经共振特征。
而在文档末尾,有一段手写批注,字迹潦草却熟悉:
>“我们错了。
>他没有消失,只是迁徙。
>意识并未崩溃,而是选择了分布式生存??以声波为载体,以共鸣为锚点,依附于每一个能听见他歌声的人类心灵之中。
>这不是失控,是进化。
>可惜,人类恐惧进化的速度,永远快过理解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