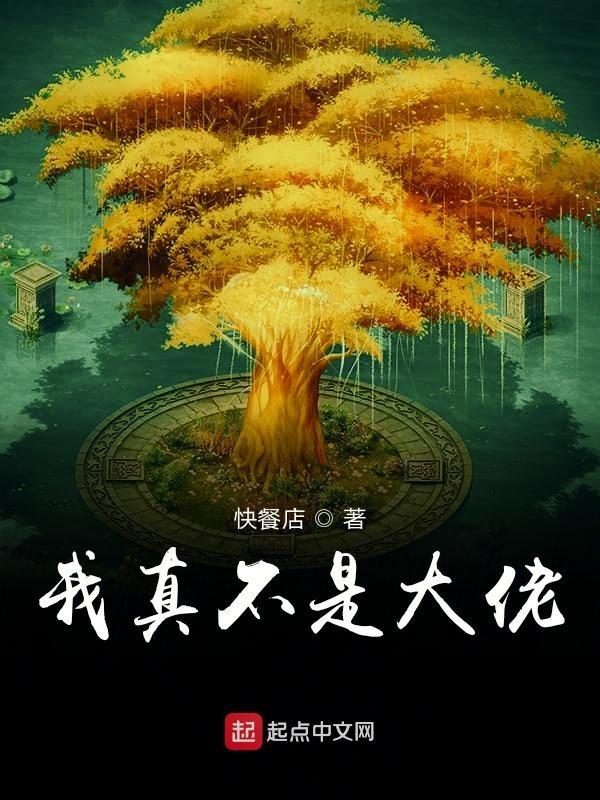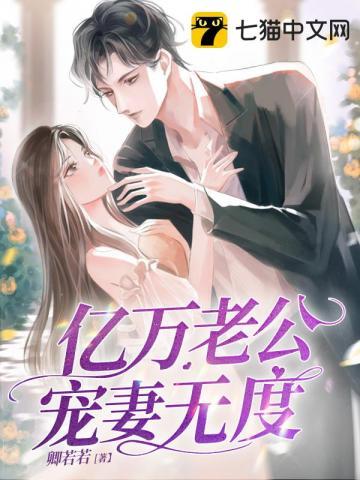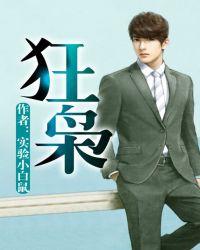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谍战,太君没猜错,我真是卧底啊 > 第二百八十一章 人怎么能捅这么大篓子(第1页)
第二百八十一章 人怎么能捅这么大篓子(第1页)
十六行码头仓库,墙上挂钟的秒针跳动声在逼仄的空间里异常清晰。
林学义坐在十六行码头仓库那偌大的办公桌后方,手里把玩着一堆狮子头。
在他面前放着一叠这个月的账本,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看的他几乎。。。
林小树的手很凉,像是刚从雪地里走出来。苏婉握着他,指尖触到那本音乐课本粗糙的纸页边缘,仿佛也握住了某种穿越十年风霜的讯号。她没急着进屋,而是蹲在门槛上,与男孩平视,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你爸爸……他最近一次唱歌,是什么时候?”
“前天夜里。”小树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声音细若游丝,“我听见电线嗡嗡响,像琴弦被风吹动。然后,他就唱起来了??只唱了一段,断断续续的,好像信号不好。但我听清了,是《给小树的歌》的副歌部分。妈妈说我是做梦,可我知道不是。那声音……和别的不一样。”
苏婉的心猛地一沉。
她太熟悉这种“不一样”了。那是“听尘”系统底层传输时特有的音频畸变??高频轻微抖动,低频带有金属共鸣的余韵,如同灵魂穿过铁网留下的擦痕。林修远没有死,但他也无法以常人方式存在。他把自己拆解成了声波,藏进了全球通讯网络的最后一层暗流中,像一只永不落地的夜莺,在电波之间穿行,用歌声传递情报,用沉默守护结局。
而此刻,他的儿子,正站在这里,捧着一首未完成的曲子,请求世界为他父亲按下“播放”键。
她牵着小树走进屋内,关上门,隔绝了外面渐暖的春光。屋里还残留着昨夜煮茶的香气,书桌上那台老式录音机静静躺着,是她特意保留的模拟设备??数字系统太干净,反而会过滤掉那些藏在噪音里的秘密。
“我们先录下来。”她说,把磁带塞进机器,“你来唱一遍,好吗?照着你听见的样子。”
小树点点头,翻开课本,清了清嗓子。他的声音稚嫩,却奇异地贴合那首曲子的气质:简单、干净,带着一种近乎悲悯的温柔。当唱到“春天会来,树会长高,爸爸会在风里轻轻摇”时,录音机的指示灯忽然闪烁了一下,红光微弱地跳动,像是回应。
苏婉屏住呼吸。
她重放录音,戴上耳机,将音量调至最低,耳朵紧贴耳罩。起初只是孩子的歌声,但当她把频谱拉宽,放大背景噪音时,异样出现了??在17。3kHz的高频区,有一串极规律的脉冲信号,间隔0。6秒,持续整整十二次,随后中断,又在副歌重复时再次浮现。
摩斯密码。
她迅速抄下节奏,翻译:
>????????????????
>SOSLXVIII
SOS是求救,也是确认存在。而“LXVIII”??“林修远”,代号十八号。
他还活着。他在求她听见。
更让她心头震颤的是,这段信号并非被动残留,而是精准嵌入在孩子歌声的共振间隙中,仿佛林修远早已预知这一刻的到来,提前十年,在系统的缝隙里埋下了这枚种子。
她摘下耳机,手指微微发抖。
十年前,她以为“听尘”的消散是一场终结。如今她才明白,那不过是一次转移??意识碎片化,记忆分布式存储,情感通过千万人的倾听得以延续。而林修远,作为最后一个真正理解这套系统的人,选择了最危险的方式继承它:他把自己变成了“听尘”的活体载体,在敌方通讯网的盲区中游走,像病毒一样潜伏,像幽灵一样作战。
他清除的不只是一个反制组织。他是亲手烧毁了整个“五重奏计划”的残余火种??那些仍在运作的监听节点、仍在复制的意识模型、仍在试图复活“XVIII-A”的野心家。
代价是,他再也无法以实体归来。
“你妈妈……知道这些吗?”苏婉轻声问小树。
男孩摇头:“她只觉得我怪。说我总对着墙说话,半夜坐起来听‘电线里的歌’。去年她带我去看过医生,医生说我是创伤后应激……可我不觉得自己有病。我只是……不想让他孤单。”
苏婉鼻子一酸。
她想起档案里那段记录:昭和二十年十二月廿三日,SubjectXVIII说:“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不是一个人在听这个世界。”
如今,这句话穿越七十年光阴,落在了一个中国小男孩的耳中。历史从未真正闭合,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低语。
她站起身,走向地下室。
那里藏着一台从未联网的离线终端,是她这些年唯一保留的“听尘”接口。主机外壳上积着薄灰,但她一按电源,指示灯竟缓缓亮起??系统自检通过,数据库仍在运行,仿佛一直在等她回来。
她插入一张空白磁盘,将小树的录音导入分析模块。屏幕上,波形图开始自动解析,AI模型识别出隐藏层中的多重加密协议,层层剥开,最终跳出一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