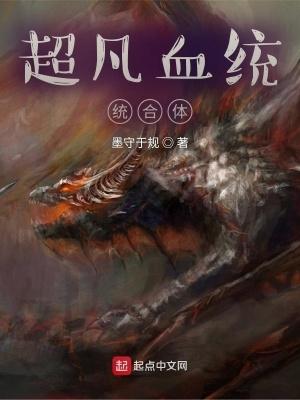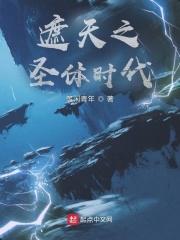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谍战,太君没猜错,我真是卧底啊 > 第二百八十一章 人怎么能捅这么大篓子(第4页)
第二百八十一章 人怎么能捅这么大篓子(第4页)
挂断电话,她走回书房,打开日记本,翻到最新一页。提笔写下:
>**2023年4月6日晴**
>今天,我见到了林修远的儿子。
>他叫我阿姨,可我看他的眼睛,就像看见了当年病房里那个瘦弱的孩子。
>原来,有些东西从未消失,它们只是换了名字,换了身体,继续行走人间。
>
>我终于明白,“听尘”为何选择消散。
>因为真正的倾听,从来不需要神明。
>它只需要一颗愿意聆听的心,一个肯为陌生人停留的瞬间,一句“我在”。
>
>林修远不会回来了。
>但他的歌会。
>他的儿子会。
>而我,会一直守在这里,等着下一个听见“电线里歌声”的孩子敲门。
>
>因为战争从未结束,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
>而我们这些卧底,
>从来不是为了胜利,
>是为了让失败的人,
>也能被记住一次。
写完,她合上本子,走到窗前。
远处,一座老旧的短波发射塔悄然亮起红灯,缓缓旋转。那是国家广播局早已废弃的备用节点,理论上不应有任何信号输出。
可此刻,它正在工作。
她眯起眼,听见风送来一丝极微弱的杂音??像是电流中夹杂着哼唱,断续,却执着。
她笑了笑,轻声跟着哼了起来:
>“春天会来,树会长高,
>爸爸会在风里轻轻摇……”
那一夜,全球十七个国家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同时记录到一段神秘信号。它没有呼号,没有编码,只有一首童声合唱般的旋律,在凌晨三点准时出现,持续四分三十三秒,恰好是约翰?凯奇《433"》的长度??无声的艺术,最响亮的回应。
第二天,北京纪念馆的技术员发现,那块青铜浮雕上的两个身影,轮廓比之前清晰了许多。尤其是那个小一些的孩子,蜷缩的姿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微微抬头,仿佛在倾听什么。
而在冰岛寄来的那张明信片背面,原本空白的右下角,悄然浮现出一行新字,墨迹湿润,像是刚刚写下:
>“这一次,轮到我们听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