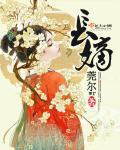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激情年代:开局成为七级工程师 > 第三十八章 父女避讳(第3页)
第三十八章 父女避讳(第3页)
她靠在他肩上,许久才说:“你说,以后还会有人记得她们吗?”
“也许不会。”林远望着远去的光点,“但只要还有人敢在深夜独自流泪,敢在人群中保持沉默,敢在分享之前先问自己是否愿意??她们就从未真正离开。”
那天之后,全球多地陆续报告类似现象:东京湾夜空中浮现短暂的人形光影;撒哈拉沙漠某处沙丘自动排列成古老的握手符号;格陵兰冰川断裂时,声波分析竟还原出一段早已失传的因纽特摇篮曲。
医学界将这种跨越地理与媒介的集体感应命名为“余响效应”??意为重大精神变革完成后,文明本身所释放的最后一道回声。
与此同时,“记忆储蓄池”迎来新一轮升级。新版界面取消了热度排行、推荐算法和情绪标签,改为纯手动浏览模式。用户需输入特定关键词或情感色调才能检索内容,且每次访问都会收到提示:
>【您即将阅读的记忆,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请以敬畏之心进入。】
更有意思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删除自己过去的共感记录。不是出于后悔,而是觉得“那段情绪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一位作家公开销毁了自己曾广受赞誉的“战争创伤共感作品集”,理由是:“当年我只是为了获奖而复制别人的痛,现在我想写点真正属于自己的故事。”
一年后,第一所“断链学校”在云南建立。
这不是反科技的隐居营地,而是一所新型教育机构,课程核心理念是:“培养能在连接与独处之间自由切换的人。”孩子们每天有两小时必须关闭所有电子设备,在森林中行走、冥想、写作或交谈。他们学习如何分辨“我想分享”和“我应该分享”的区别,也练习在群体中保持自我边界。
林远受邀担任名誉顾问。开学典礼那天,他给学生们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有个男孩,特别害怕孤独。他总觉得,只要没人看着他,他就不存在了。所以他拼命刷存在感,上传每顿饭、每个笑容、每滴眼泪。直到有一天,他病了,躺在床上发高烧,所有人都看不见他,也没人给他点赞。那一刻他突然发现,尽管身体虚弱,但他依然能感受到窗外的风,能听见母亲哼歌的声音,能想起小时候摔跤后自己爬起来的那种倔强。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我不是因为被人看见才存在,而是因为我能感受,所以我活着。”
台下一片安静。
有个小女孩举手问:“叔叔,那你现在还怕孤独吗?”
林远笑了:“怕啊。但我学会了和它做朋友。就像冬天里的火炉,太近会烫伤,太远又冷。最好的距离,是能看清它的脸,又不至于被吞噬。”
掌声响起。
典礼结束后,苏岚在校门口等他。她递过一杯热豆浆,笑着说:“听说今晚天文台又要发射新信号了?”
“嗯。”林远接过杯子,“这次不是回复外星文明,而是向太阳系边缘发送一批‘人类日常档案’,作为未来可能的文明火种。”
“内容呢?”
“全是琐碎小事。”他说,“比如一个妈妈给孩子扎辫子的手法,街头艺人弹吉他跑调的瞬间,地铁里陌生人让座时的那个微笑……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生活本身。”
苏岚点头:“这才是最难复制的东西。”
当晚,两人并肩坐在屋顶看星星。远处传来孩童追逐嬉戏的声音,近处是屋檐下风铃轻响。林远忽然说:“我昨晚做了个梦。”
“梦见什么?”
“梦见我们老了,住在一个小山村,门前有棵大槐树。你总坐在树下织毛衣,我则在旁边修收音机。有一天,收音机突然响了,播放的正是八十年代那首民谣??就是周明璃最后听的那首。”
苏岚侧头看他:“然后呢?”
“我没修好它。”他笑着,“但我俩就这么听着,一句一句,直到电池耗尽。”
她靠在他肩上,轻声说:“那一定很美。”
的确很美。
因为在那个梦里,没有人急于证明自己存在,也没有人恐惧被遗忘。他们只是安心地活着,像大地上的草木,像夜空中的星辰,像每一盏在黑暗中独自发光却不求回应的灯。
而这,正是周明璃所说的??
真正的激情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