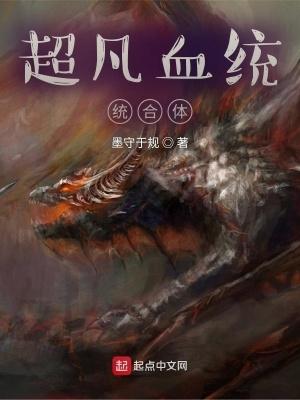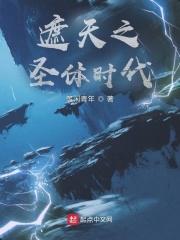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儒道玄途 > 第三百零二章 两败俱伤(第2页)
第三百零二章 两败俱伤(第2页)
一位年轻女医官迎上来,是许观衡的学生,姓柳。她恭敬行礼:“启先生,昨日有位病人苏醒了。”
“失语症?”启声问。
“不,是‘反语症’。”柳医官神色凝重,“他能说话,但每一句都与心意相反。想说‘我爱你’,出口却是‘我恨你’;想哭,却大笑不止。我们查了他的经历,发现他曾是伪言教余孽的‘言刑官’,专门用扭曲语言逼供犯人……可三年前一场大火后,他就疯了。”
启声随她走入内室。
病床上的男人约莫四十岁,面容枯槁,双眼却异常清明。见启声进来,他猛地坐起,嘴唇剧烈抖动,终于挤出一句:“你……真丑。”
启声不怒,反而走近一步:“你说反了。”
男人浑身一震,眼中闪过一丝痛苦。
“你想说的是‘你很美’,或是‘你救了我’。”启声轻声道,“可你的舌头背叛了你的心,因为当年你用它伤害了太多人,所以现在,它拒绝再为你服务。”
男人突然嚎啕大哭,可发出的却是尖锐笑声,令人毛骨悚然。
启声闭眼,伸手按在他额上。刹那间,她感知到对方意识深处有一团黑色漩涡,正不断吞噬真实情感,将其翻转为谎言。这不是普通的心理创伤,而是伪言母体残留的“逆言种”在作祟??它并未死去,而是以“反向共情”的形式寄生在那些曾滥用语言的人身上。
“它在报复。”启声睁开眼,“它让施害者亲尝自己种下的苦果:你想真诚,却只能虚伪;你想忏悔,却只能嘲讽。”
当晚,她在疗堂静室写下《反言解契》九章,提出一种新的治疗方式:不是矫正语言,而是重建“言与心的距离”。她认为,当一个人长期用语言伤害他人,他的心灵会自动与言语脱钩,形成“言壳”??就像龟鳖缩入硬甲,再也无法触碰真实。
“要治此症,须先让他重新学会‘说错话’。”她在笔记中写道,“允许他结巴、重复、语无伦次,甚至胡言乱语。唯有如此,才能打破完美表达的执念,让心重回话语之前。”
三日后,她亲自为那名男子弹奏冰弦琴。
琴音不成调,只是随意拨弄,时断时续,像孩童初次触弦。她一边弹,一边喃喃自语:“我今天吃了豆腐……我觉得有点咸……其实我不想吃……但我怕厨娘难过……所以我没说……你看,我也常把话说假。”
男子呆呆听着,忽然咧嘴笑了??这次是真的笑。
接着,他嘴唇微动,声音沙哑:“我……我想……妈妈……”
泪水顺着他脸颊滑落。
启声点头:“你说错了也没关系。她听得见的。”
消息传开,越来越多“反语症”患者涌入京师。有人曾是朝堂辩士,出口成章却从未吐露真心;有人是市井媒婆,一生撮合姻缘却从不说爱;还有人是刺客,任务完成前必须发誓“此心无愧”,实则夜夜梦魇。
启声一一接见,不施药,不念咒,只与他们闲谈琐事,任其胡言乱语。她说:“言语本就不该总是有用。废话、傻话、气话、梦话,都是活着的证据。”
与此同时,第七星的闪烁愈发频繁。
许观衡连夜测算,发现其明灭规律竟与《未来书》最初的预言频率一致??每三十六息一次,恰是人类平均呼吸周期的整数倍。更惊人的是,若将这些闪烁转化为音波,会形成一段极低频的吟诵,内容竟是《孤雏引》的倒序版本。
“它在复读。”许观衡找到启声时,声音发紧,“它想重启语界幽壤的共振场。”
启声坐在观星塔顶,手中把玩着愿言铃。月光洒在她脸上,映出淡淡的倦意。
“它不怕光,也不怕火。”她忽然说,“它怕的是‘无意义的话’。”
许观衡一怔。
“你发现没有?”她抬头,“自从万语复苏,人们说话越来越多,可真正重要的,往往仍是那几句笨拙的、重复的、甚至不合时宜的??比如‘我在这里’,比如‘别怕’,比如‘我们一起’。伪言母体追求效率,消灭冗余,可人类最深的情感,偏偏藏在那些‘多余’的停顿与?嗦里。”
许观衡若有所思:“所以你要让它听见‘废话’?”
启声点头:“我要办一场‘无用言集’。”
七日后,京师广场搭起高台,宣布举办首届“废话大会”。不限身份,不论内容,只要愿意开口,便可登台说任何无关紧要的话。百姓初时不解,继而哄笑,再后来,竟排起长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