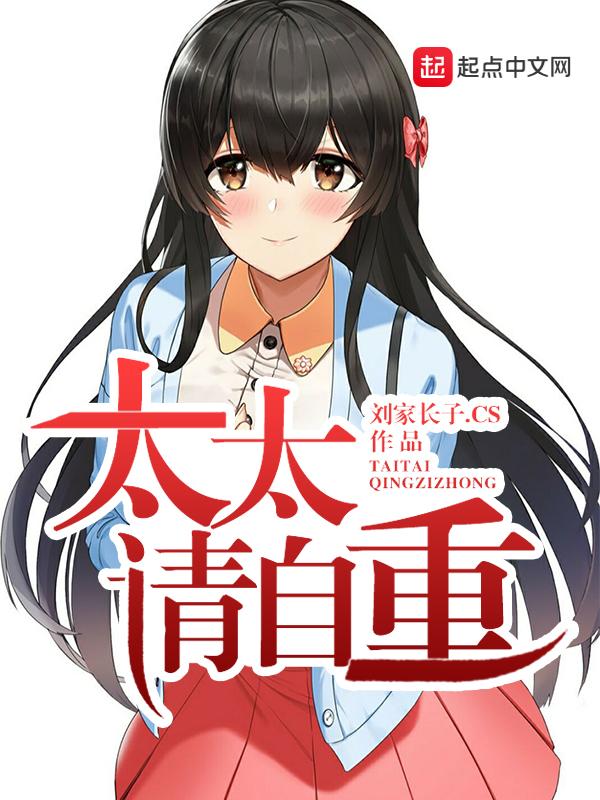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大明第一国舅 > 第697章 争权夺利(第2页)
第697章 争权夺利(第2页)
尹德惠凝视侄儿良久,终是朗声大笑:“好!这才是帝王之资!舆论之势,胜于千军万马!”
七日后,《江南新政日报》首期问世。头版赫然写着:
【昆山周庄陈氏主动申报隐田八百亩,税额由每年三石增至八十石;吴县太湖渔户王阿牛,原负担丁银五两,今按新规减免七成;苏松三府首批济民工坊开工,收容流民一万两千人,日供两餐,月付工钱……】
文末署名:“百姓之声,天下共听。”
消息如野火燎原,短短十日,报纸传遍江南十余州县。更有读书人自发誊抄,贴于学堂、茶馆、驿站门前。一些原本观望的中小地主开始陆续自首申报,唯恐落后一步,反被清算。
而此时,沈万昌等人策划的“赴京告御状”队伍才刚走到镇江,便发现沿途舆情完全失控。他们雇佣的“苦主”一露面,立刻被人认出是某豪族家奴,当场遭百姓唾骂驱逐。更有好事者高喊:“你们不去告贪官,反倒帮地主喊冤?羞也不羞!”
队伍溃散,密谋破产。
京中,朱元璋连续三日召见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询问江南动态。詹徽如实奏报:“据各地塘报,苏松百姓初有疑惧,然近月以来,因新政得利者日众。尤以济民工坊最为称颂,许多流民感激涕零,称‘朝廷救我一家性命’。臣以为,此非虚饰之词,实乃民心所向。”
朱元璋沉默良久,忽然问:“尹德惠那小子,最近可有异动?”
詹徽一怔:“回陛下,尹国舅闭门理事,除公务外不见宾客,连太子府也少去。其子尹文昭日前娶妻,宾客不过三十人,连礼部官员都没请。”
“哼。”朱元璋冷笑,“越是这般,越显得干净。朕不怕有人做事,就怕有人做戏。马祖佑那边呢?”
“马钦差已于昆山设立‘巡按司’,亲自审理阻挠新政案件。截至目前,共查处贪官十七人,豪强十三户,抄没隐田逾六万亩,其中半数已重新分配给无地农户。”
朱元璋缓缓点头,终是吐出一句:“看来,这局棋,他们走得比朕想象的还要稳。”
可就在此时,一道急奏从云南飞驰而来:傅友德报称,当地土司叛乱平定,缴获敌营文书多份,其中一份赫然提及“江南事成,则南北呼应,共图大计”,而落款印章,竟是已被软禁于凤阳的胡惟庸旧部!
朝野震动。
朱标连夜召见尹德惠:“父皇已下令彻查胡党余孽,锦衣卫正在搜捕涉案人员。若此事属实,说明反对新政的力量,早已超出地方豪强范畴,甚至可能牵连中枢!”
尹德惠面色凝重:“恐怕不止如此。胡惟庸虽倒,但他当年主张‘集权六部’的理念,仍有不少官员暗中认同。这些人不满当今分权于太子、国舅之势,视新政为尹家揽权之具,故不惜勾结内外,欲掀翻大局。”
“那你打算怎么办?”朱标直视他眼睛。
“反击。”尹德惠声音低沉却坚定,“既然他们要把经济改革变成政治斗争,那我们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雷霆手段。”
次日,尹德惠联合郁新、詹徽,联名上疏,请设“新政特别法庭”,专审阻挠改革、煽动民变、勾结宦官、通敌谋逆四大罪。该庭直属皇帝,不受三法司节制,允许钦差异地提审、跨省缉拿,且判决无需复核,即时执行。
朱元璋览奏,提笔朱批八字:“准奏。胆敢阻拦者,杀无赦。”
圣旨下达当日,南京城外血光冲天。
马祖佑依令行事,先将松江知府以“纵容属员焚毁粮册、勾结商会抗税”罪名革职下狱;继而在苏州查获“恒丰号”地下账本,顺藤摸瓜,牵出刘瑾收受白银十二万两的确凿证据。更令人震惊的是,账本中竟有数笔款项流向太子府某位低级属官,疑似企图栽赃朱标!
尹德惠当机立断,奏请隔离审查该属官,并公开其供词。真相揭晓:此人原系刘瑾门生,私自接受贿赂,伪造文书,意图陷害太子。朱元璋震怒,当即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家属流放琼州,涉案豪强一律抄家灭族。
一场席卷朝野的风暴,在铁血与智谋交织中渐渐平息。
三个月后,苏松常三府首期清丈完成。数据显示:新增登记耕地四十八万亩,年税收反较往年增加一成二;济民工坊带动就业超五万人,民间械斗案件下降七成;更有数百名秀才联名上书,请求将摊丁入亩写入《大明会典》,永为定制。
春风吹过江南,新秧遍野。
马祖佑站在昆山城头,望着远处阡陌纵横、农夫耕作的景象,久久不语。身旁副官低声问道:“大人,下一步去哪儿?”
他收回目光,淡淡道:“去常州。那边还有二十个县等着清丈。”
远方,一艘官船正破浪而来,船头插着一面黄旗,上书两个大字:**钦差**。
与此同时,京城东宫。
朱雄英合上最新一期《江南新政日报》,轻轻搁在案上。窗外,紫禁城的晨钟悠悠响起,新的一天开始了。
他转身取出纸笔,开始撰写一篇新的策论,题为:《论制度与监督之共生关系》。
而在千里之外的凤阳,一座幽静别院内,一位白发老者倚窗而坐,手中摩挲着一枚残破的玉佩,喃喃自语:“变法……终究还是开始了么?只愿这一次,莫再重蹈我的覆辙。”
雨过天晴,云开雾散。
大明的天空,正悄然酝酿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