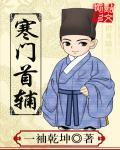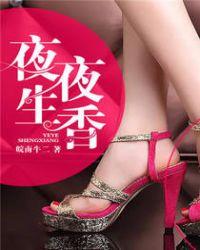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死后,妻子浪翻了 > 第1454章 我是林江河(第2页)
第1454章 我是林江河(第2页)
我站起身,绕过桌子走到她面前,伸出手:“这部片子,星辰娱乐全额投资。不限预算,不限周期,我要它完整呈现。另外,成立专项基金,资助类似题材的青年创作者。名字就叫‘归岸影像计划’。”
她愣住了,眼眶瞬间红了。
走出会议室时,陈默跟了出来。我们在天台抽烟,谁都没说话。风吹得衣角猎猎作响,远处高楼林立,霓虹闪烁,可我们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岁那年,在78号楼顶谈论未来。
“你觉得我们做到了吗?”他问。
“什么?”
“当年说的??只捧真心做艺术的人。”
我望着天边渐暗的晚霞,轻轻点头:“至少,有人开始相信这件事了。”
几天后,《归岸》短片样片上线内部平台,反响远超预期。员工自发转发,留言区刷满“我也曾迷失过”“谢谢你替我说出了心里话”。更有十几所高校影视系联系公司,希望组织学生观影交流。媒体再次聚焦林江河,称这是“资本回归人文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但我更在意的是另一件事。
那天傍晚,我收到一封来自瑞士的信。信封很旧,邮戳显示寄出时间竟是八年前。拆开一看,是陈默母亲的笔迹:
>“江河:
>
>默儿常说,你是他唯一相信不会变的人。这些年他在异国照顾我,夜里常常画画,画你们小时候的模样。他知道你走了另一条路,但从没怪过你。临终前,他让我一定要把这幅画交给你。
>
>??附页是他最后完成的一幅作品。”
我颤抖着翻开附件。
那是一幅水彩画:两个少年并肩走在雨中,伞斜斜地遮住彼此的头。背景是模糊的城市轮廓,前方却有一道光刺破乌云。画角写着一行小字:
>“无论走多远,记得有人一直在等你回来。”
泪水再一次模糊视线。我拨通陈默电话,接通那一刻,竟像个孩子般哽咽:“你妈……她……”
“我知道。”他的声音平静而温柔,“她走得很安详。她说,终于可以把最重要的东西托付给你了。”
挂掉电话后,我坐在书房整整一夜。第二天清晨,我写下一封信,寄往全国三十位曾因坚持创作而被迫离开行业的艺术家。信中只有两句话:
>“你们没有错。
>
>欢迎回家。”
与此同时,“归岸计划”全面升级。除了资金支持,我们增设“心灵创作营”,邀请心理学家与艺术导师共同参与,帮助创作者梳理内心创伤。第一批入选者中,有一位叫李砚的诗人,曾因抑郁症隐居山中十年,靠抄经度日。当他接到我们的邀请函时,回复只有一行字:
>“我以为诗死了,原来它只是睡着了。”
三个月后,《归岸》正式公映。首映礼选在城南老电影院举行??正是当年我和陈默省吃俭用去看文艺片的地方。门口挂起巨幅海报,主角背影与我年轻时几乎一模一样。观众席坐满了人:员工、艺术家、心理医生、康复中的病人,还有许多素不相识却深受触动的灵魂。
电影结束时,全场寂静。随后掌声如潮水般涌来,持续了整整十分钟。
童欣握住我的手:“你看,你早就影响了很多人。”
我摇头:“不是我,是我们。是你唱的那首歌,是陈默画的那幅画,是苏念拍的这部电影,是每一个不肯放弃真实自我的人,一起完成了这场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