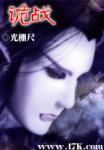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宗门:从领悟雷法开始 > 第866章 谁赞成谁反对求月票(第2页)
第866章 谁赞成谁反对求月票(第2页)
突然,天空阴沉,乌云压顶,却无半点雷声。众人抬头观望,只见北斗七星缓缓移位,继而七颗星辰同时爆发出璀璨金光,交织成一行悬浮于空的文字:
**“念真安否?”**
全场寂静。
周承远怔住,眼眶瞬间湿润。他知道,这是守忆之坛的回应机制??唯有当集体记忆达到某种共鸣阈值时,地脉雷纹才会触发星象异变。而这一次,问题竟是关于一个人的安危。
“老师……”他低声呢喃,“您还在听着啊。”
三日后,消息传来:周念真病重卧床,已无法言语。她在临终前唯一的要求,是将她的遗体运回守心林火化,骨灰撒于桃树之下。
周承远亲自护送灵车北上。途中遭遇暴风雪,车队寸步难行。就在众人准备弃车避难之际,忽见前方风雪中走出一名盲眼老妇,手持竹杖,身后跟着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她正是当年那位抄经人之徒,如今已是南方“补遗斋”的主理人。
“我知道你们要去哪。”她说,“我也要去。”
于是两支队伍合并前行。奇迹般地,越是深入雪域,风雪越是减弱。待抵达守心林时,竟晴空万里,暖阳照面。
葬礼简单而庄重。没有哀乐,只有孩童们围坐林间,轮流朗读《实录》中最动人的一章??《焚书之夜》。当读到“柳芽撕开心脏,放出银光”时,整片桃林无风自动,花瓣纷飞如雨。
夜深,周承远独自守在火堆旁。忽然,地面微震,那口埋藏多年的陶罐自行出土,贝壳铃铛凌空升起,悬于火焰之上。铃身泛起玉色光泽,随即传出一道极轻、极远的声音:
“谢谢你,替我看了这么多年的春天。”
他猛地抬头,泪水滑落:“老师,您放心。我会继续走下去。”
铃铛轻轻一晃,坠入火中,化作一点银星,融入灰烬。
次日黎明,桃林中央冒出一株新苗,通体晶莹如琉璃,叶片边缘泛着淡淡雷光。当地老人说,那是“信木”,百年仅生一株,唯有守心之人死后方可催生。
又五年,朝廷内部再起波澜。有大臣奏请删改《实录》部分内容,称“过于激愤,不利安定”。皇帝犹豫未决,命内阁议政三日。
第四日清晨,紫宸殿外雷声炸响,一道紫电直击金銮殿匾额,将其劈成两半。断裂处显出四个血红大字:
**史不可断**。
满朝震惊。太史令连夜查验天文志,发现那一夜北极星剧烈闪烁,其光谱竟与百年前柏青书写第四字“义”时完全一致。
自此,无人再敢提删书之事。
与此同时,海外诸国也开始流传“东方有圣者,以心为笔,以雷为证”。不少异邦学子慕名而来,欲求学于慈恩学堂。其中一人名为阿兰陀,来自极西之地,肤色黝黑,言语不通,却坚持每日抄写《实录》一页,风雨无阻。
十年后,他成为第一位外籍守心使,在西域重建“净心会”旧址,立碑铭曰:“吾非华人,但信真理。柏青之道,不在血脉,而在人心。”
再三十年,天下太平,忆园遍布城乡,孩童入学第一课便是背诵五字箴言。雷法不再神秘,许多修士发现,只要心怀“信愿”,便能在雷暴中感应到一股温和力量,助其突破瓶颈。世人称之为“引信渡劫”。
更有奇者,每逢清明雷雨,各地碑石自动浮现新人名??那些默默守护记忆却从未留名的普通人:某个山村教师,二十年如一日向学生讲述真相;某位狱卒,冒险保存囚犯口述史料;甚至一名乞丐,临终前将藏有《实录》残页的讨饭碗交予路人……
他们的名字,终于被天地铭记。
这一年的记日大典格外隆重。百万民众齐聚京都忆园,仰望星空。北斗再次移位,勾勒出执笔人形,而后虚空浮现五个新字:
**我们在守**。
不同于百年前那一句孤独的“我在守”,如今的宣告,是千万人共同意志的回响。
仪式结束后,一个小女孩拉着母亲的手问:“妈妈,柏青先生长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