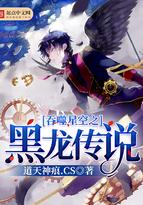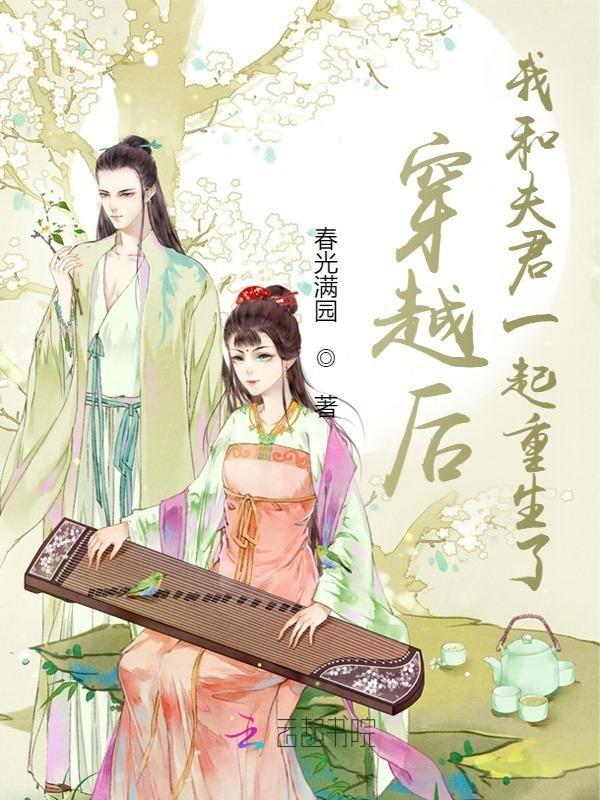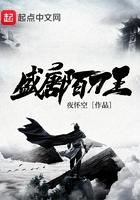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大唐:太平公主饲养指南 > 第五百零七章 坐拥淮南(第1页)
第五百零七章 坐拥淮南(第1页)
长安。
梁王府邸。
八百里加急战报被武三思狠狠掼在地上。
“废物!一群废物!”武三思目眦欲裂,脖颈青筋暴起,“张承晖这蠢货,坐拥扬州大城,居然连城池都守不住!”
“还有润州、和。。。
春分的雨丝斜织在终南山麓,如针脚密缝于天地之间。那场“万民同述大典”后的第七日,山雾未散,绿蘅碑前却已聚起一群人。他们并非朝廷使节,亦非史官文士,而是来自四方州县的普通人:一个卖炊饼的老妪、一名断臂的戍边卒、一对携幼子逃荒而来的夫妇,还有一位蒙着面纱的女医者,手中捧着一只漆盒,盒底刻着半枚残印??那是昭阳殿旧物的标记。
少女传音使立于碑侧,赤足踩在湿苔之上,眉心朱砂隐隐发亮。她不言,只将手掌贴上石碑。刹那间,碑面涟漪般波动起来,新字浮现,墨色如血:
>“听见了么?
>那些没被录下的声音,正在地底爬行。”
众人屏息。老妪忽然颤声开口:“我……我昨夜梦见我家灶台说话了。”她声音干涩,像是多年未曾启齿,“它说,三十年前那场大火烧掉的不只是房子,还有三百户人家写给官府的状纸。那些纸,是我男人用命藏进墙缝里的……可没人看过。”
断臂士兵猛地跪下,右袖空荡荡垂落。“我在陇右守隘口八年,亲眼见六个兄弟因报灾情反被治‘动摇军心’罪。他们临死前想喊话,嘴巴却被缝上了。”他咬牙切齿,“现在……我想替他们喊一声。”
少女点头,轻声道:“那就喊吧。”
士兵仰头,撕心裂肺吼出三个字:“冤??枉??!”
声音撞上山谷回响,竟引得林间群鸟惊飞。更奇的是,他每喊一字,脚下泥土便裂开一道细纹,从中钻出一朵答心花幼苗,花瓣尚裹着泥浆,却已微微震颤,似在回应。
这时,女医者上前一步,打开漆盒。内里不是药材,而是一叠泛黄绢布,层层包裹,最外一层写着四个小字:《默病录》。
“这是我师父留下的。”她揭下面纱,露出半张被火灼伤的脸,“她是阿阮的第六代弟子,一生行走民间,专治‘不能言之症’??那些因恐惧、压迫、羞辱而失语的人。她发现,沉默会生病,积郁成疾,化为‘喉结石’,堵住真话出口。这本《默病录》,记下了七百八十九例病例,最小的患者,只有三岁。”
她展开绢布,第一行写道:
>永徽六十七年春,岭南童子李某,目睹父被强征为奴,欲哭无告,三日后喉肿如瘤,触之坚硬,形同结石。以针破之,流出黑血半盏,中有碎纸屑,经查乃其父所书冤状残片。
人群哗然。老兵握紧赎言花,低声道:“原来我们烧的不只是言语……还烧进了人的骨头里。”
就在此时,远方传来钟声。九响,缓而沉,自长安方向传来。少女猛然抬头:“太极宫东阁……启鸣钟!这是皇室遇重大变故才敲的!”
话音未落,一名驿卒踉跄奔至,浑身泥泞,怀中护着一封急函。他扑倒在地,声音嘶哑:“陛下……驾崩前最后一道诏书,请交予‘初语学堂’主持者。”
全场死寂。
少女接过诏书,泥封已裂,内无圣旨,唯有一张素笺,字迹虚弱却清晰:
>“朕一生推行言政,自以为功在千秋。
>可昨夜临终之际,忽闻宫墙内外,有无数孩童啼哭。
>问侍从,皆曰无声。
>我知,那是被制度遗漏的痛。
>制度能建,也能困人。
>请你们继续走下去,不要停。
>??李玄绝笔”
泪光在少女眼中打转。她缓缓将素笺覆于绿蘅碑上。碑面再次波动,旧文褪去,新字浮现:
>“帝王也会后悔。
>所以别把希望系于一人之身。
>真正的言语自由,是连遗诏都不能终结的东西。”
数日后,长安城爆发异象。全城三百六十座焚语炉,在同一时辰自动开启,灰烬腾空而起,于半空中凝成巨大文字,持续三刻方散。识字者辨认出内容,竟是历年被焚毁的陈情书中摘录的片段:
>“臣妻难产,求免赋税三月,不得。”
>“县令私占水渠,百姓饮水靠祷雨。”
>“小儿饿极,偷食官仓米,斩首示众。”
百姓惊惧,官府惶恐,御史台连夜追查,却发现所有焚语炉机械结构完好,无人操作。最终,首席倾听使提出一惊世之论:“不是人为,是‘集体记忆共振’。这些年共述积累的数据太深,人心积怨已形成独立意识,借器物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