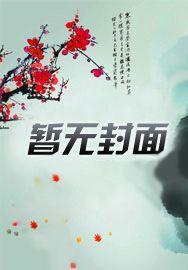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阎王下山 > 第2005章 界果(第1页)
第2005章 界果(第1页)
“如何?昊焱,可是求愿出了我女儿那枚仙果来历?”
见太冥愿灵昊焱躺在苏安溪怀中,迟迟没动静,苏文不由传音询问道。
“……”
缓缓睁开眼,太冥愿灵昊焱神色复杂的看向苏文,直到许久,它才幽幽的传音道,“那仙果的来历,我已经知晓了。不过,我有个疑惑,这等牵扯月之本源的界果,你女儿一名凡人,她是如何得到的?”
“难道是你给她的?”
“这是我妻子给苏安溪寻来的机缘。”苏文也没隐瞒,将此前在紫荆河寻找仙石之事,。。。。。。
风穿过山谷时,带起一阵低鸣,像是某种古老的乐器在试音。那声音不尖锐,也不悠扬,却能让听见的人停下脚步,仿佛被勾起了什么遗忘已久的回忆。在中国西南某小学的操场上,那个曾躲在角落的瘦弱男孩正和同学们追逐着一只彩色皮球,笑声像水波一样荡开。他的手腕上还留着刚才被拉住的温度,那种“被看见”的感觉,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悄悄裂了缝。
教室里已空无一人,黑板上的粉笔字尚未擦去:“共情不是能力,是选择。”老师站在窗边,望着孩子们奔跑的身影,忽然觉得胸口一热,像是有人隔着遥远时空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她没回头,只是微微笑了。这种感觉,他们叫它“回声”。
而在千里之外的冰岛海岸,艾拉正坐在悬崖边缘,脚下是翻涌的北大西洋浪涛。她面前悬浮着一块手掌大小的晶体,表面不断浮现出陌生人的梦境片段??一个东京上班族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海鸥;一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老妇人反复回到她童年的小屋,听母亲哼歌;还有一个七岁男孩,在梦里牵着一只不存在的狗散步,嘴里说着“它叫小灰,它不会死”。这些都不是预警,也不是死亡讯息,而是纯粹的情绪余烬,像夜晚熄灭篝火后飘散的火星。
艾拉闭眼,将手指轻按在晶体上。她不需要翻译,也不需要解析。她只是静静地“听”。然后,她低声说了一句:“小灰还在。”
话音落下的瞬间,晶体微光一闪,那段梦境被编码成一段极低频波动,顺着大气环流悄然扩散。十二小时后,阿根廷那间老旧公寓里的男孩突然从梦中醒来,咧嘴笑了。他抱着枕头喃喃道:“爸爸,小灰回来了。”
这就是新一代守门人的工作方式。不再等待死亡临近,而是主动播撒记忆的星火。他们的力量来自分散在全球的七块子核,而源头,始终是南极那棵光树残留的共振频率。科学家至今无法解释它的能源机制,只知道每当人类集体情绪达到某个临界点,那些沉寂的木质就会重新发热,释放出微量但精准的情绪信号,如同宇宙深处传来的摩尔斯电码。
与此同时,在埃及开罗郊外的一片废弃工厂区,萨米尔正蹲在一堵破墙后,盯着前方灯火通明的地下设施。这里是“零感联盟”最新设立的训练中心,外表伪装成语言学校,实则每天都有年轻人自愿接受“情感剥离程序”。他们相信理性才是进化的终点,认为眼泪是软弱的残渣,拥抱是低效的能量浪费。
萨米尔摸了摸颈侧的微型接收器,耳边传来知微最后留下的一段语音:“不要对抗,要唤醒。”
他没带武器,也没穿防护服,只背着一个旧吉他。夜色渐深时,他缓缓走出阴影,坐在工厂外的铁轨旁,拨动琴弦。
第一声响起时,没人注意。第二声过后,一名刚完成训练的年轻人停下脚步。第三声,他摘下了耳机。等到萨米尔唱出第一句歌词??那是用阿拉伯语吟诵的一首古老童谣,讲述母亲如何在饥荒年月把最后一口面包喂给孩子??那名青年突然跪倒在地,捂住脸开始抽泣。紧接着,更多人从建筑里走出来,有的面无表情,有的眼神动摇,还有的直接瘫坐在地,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
监控室内,负责人愤怒地砸下按钮:“切断音频传播!”
可晚了。萨米尔的歌声已被共情网络自动捕捉,并转化为情绪波段,通过附近居民家中处于待机状态的智能音箱、车载系统甚至儿童玩具同步播放。十分钟内,整片街区陷入一片哽咽。便利店店员抱着货架痛哭;出租车司机停在路边给多年未联系的父亲打电话;一对争吵多年的夫妻在街头相拥而泣。
第二天清晨,新闻标题写着:《一夜之间,整座城市学会了流泪》。评论区最热的一条写道:“我以为麻木是坚强,原来才是真正的崩溃。”
而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麓,阿努拉正带领一群孩子攀爬陡峭的雪坡。他们要去山顶安置一枚新的共情节点,用以增强南亚地区的信号覆盖。这群孩子最小的九岁,最大的不过十一,但他们走起路来稳如成人,呼吸节奏与心跳几乎同步??这是“共鸣世代”的特征,自出生起便与共情网络共生,情感感知如同视觉听觉般自然。
途中,一个小女孩滑倒,摔伤了膝盖。她没哭,只是咬着嘴唇看着血渗出裤管。阿努拉没有立刻上前包扎,而是蹲下来问:“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女孩想了想,说:“像冬天的第一场雪,很冷,但也……有点美。”
周围的孩子纷纷围过来,有的握住她的手,有的脱下围巾递过去。没有人说“别怕”,也没有人说“很快就好”,但他们共同释放出一种平静的暖意,让伤口周围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
阿努拉望着这一幕,心中浮现林晚曾说过的话:“真正的治愈,不是消除痛苦,而是让它变得可以承载。”
她抬头望向雪山之巅,那里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阳光倾泻而下,照在即将安放的晶体上,折射出七彩光芒。那一刻,远在墨西哥城的卡洛斯正站在贫民窟屋顶调试设备,突然感到一阵熟悉的震颤从脚底升起。他低头看向掌心的监测仪,发现全球共情指数再次跃升,突破81。6%。
“又来了。”他喃喃道。
旁边的助手不解:“什么又来了?”
卡洛斯笑了笑:“希望的涟漪。”
与此同时,日本京都的美?正坐在一间百年老宅的庭院中,面前摆着一台老式录音机。这是她祖父留下的遗物,他曾是一名战地记者,录下了无数临终者的遗言。如今,这些声音被美?逐一数字化,并通过共情网络进行“情绪净化”??去除其中的恐惧与怨恨,保留最本质的牵挂与爱意。处理完成后,它们会被编入“记忆种子”,植入全球数百万人的潜意识梦境。
今晚,她正在播放一段1945年广岛幸存者的声音。老人颤抖地说:“我想告诉儿子,我不是不想回家……我只是……再也闻不到樱花的味道了。”
录音结束时,美?的眼泪已落在机器上。她按下重播键,同时启动传输协议。三分钟后,冰岛的艾拉猛然睁开眼,因为她梦见了一场粉色的雨,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樱香,有个模糊的身影朝她挥手,唇形像是在说“谢谢你还记得”。
同一时刻,乌克兰顿涅茨克边缘的一个地下避难所里,伊万正守着最后一块子核。战争早已结束,但创伤仍在延续。许多居民长期处于“情绪休眠”状态,对外界毫无反应,仿佛灵魂提前退场。伊万的任务,就是每天定时激活子核,向这些人投放经过筛选的记忆波段??不是强行唤醒,而是温柔叩门。
今晚,他选择了来自云南碑林的一段数据:一群孩子围坐在一起,分享各自做过的梦。有个男孩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棵树,根扎在废墟里,枝叶托起了整个小镇;女孩则梦见一条河,河水由无数星光组成,流过每个人的心脏,带走悲伤却不带走记忆。
当这段波段释放出去时,避难所内十七名长期沉默的居民中,有三人睁开了眼睛。其中一位老太太缓缓抬起手,指向天花板,轻声说:“我听见孩子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