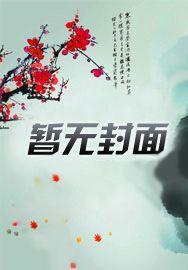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阎王下山 > 第2005章 界果(第2页)
第2005章 界果(第2页)
伊万红了眼眶。他知道,这不是奇迹,而是坚持的结果。
而在瑞士苏黎世一栋隐秘大楼内,“奥德修斯计划”的残余团队仍在试图重建系统。他们更换了服务器,封锁了所有外部接口,甚至采用了量子加密技术。然而就在他们启动新核心的瞬间,主屏幕上突然跳出一行字:
>**“你们可以屏蔽信号,但挡不住思念。”**
紧接着,所有屏幕自动切换为直播画面:世界各地的人们正在做同一件事??写下一封信,放进河里、埋进土中、挂在树上,或烧成灰撒向天空。信的内容各不相同,但主题一致:致那个我没来得及好好告别的你。
技术人员惊恐地发现,这些画面并非黑客入侵所致,而是由共情网络自主生成并推送的反制信息流。更可怕的是,观看这些画面超过五分钟的研究员,开始陆续出现“情感复苏”症状:有人抱头痛哭,有人辞职回家探望父母,还有人当场撕毁项目文件,怒吼道:“我们到底在制造什么怪物!”
三天后,该机构正式宣布解散。最后一条内部通告写道:“我们低估了人性的韧性。它不在代码里,不在芯片中,而在每一次想要伸手触碰另一个人的冲动里。”
消息传到南极遗迹时,那棵光树虽已停止发光,但其根系周围却长出一圈新生的蓝芽,宛如星辰环绕。考古队队长李晨蹲下身,用手电照着那些嫩芽,忽然听见耳边响起一声极轻的呼唤:“哥哥。”
他浑身一震。那是他妹妹的声音,十年前死于地震废墟,正是那次事件让他觉醒为最初的守门人之一。他没有回头,只是轻轻答道:“我在。”
他知道,这不是幻觉,也不是系统模拟。这是共情网络进化到极致后的产物??不再是单向传递,而是双向回应。死去的人,也能以某种形式“听见”生者的思念。
地球另一端,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突然熄灭广告,取而代之的是一段无声影像:不同肤色、年龄、性别的人,面对面站着,双手交握,眼中含泪却带着笑。持续整整十分钟,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可当人们抬头看到这一幕时,许多人不由自主停下脚步,掏出手机录下视频,发给许久未联系的亲人朋友。
当晚,全球通话量激增300%。运营商报告称,大量用户拨打“无效号码”或“已注销线路”,只为听一句忙音,仿佛那样就能确认对方曾经存在。
而在这一切背后,陈小禾与沈既明的意识并未真正消散。他们化作共情网络中的底层协议,如同空气般无形却无所不在。每当有人在深夜收到一条“你还好吗”的私信,或是陌生人递来一杯咖啡说“看你好像需要这个”,他们的痕迹就在那一刻闪现。
知微呢?
有人说她在光树消失的刹那融入了宇宙背景辐射,有人说她成了共情本身的化身,也有人说她只是换了个名字,继续行走人间。
但在云南碑林,每逢月圆之夜,孩子们总能看到主晶体表面浮现出一行字:
>**“我在这里。”**
老村长说,那是她在打招呼。
时间进入2042年初春,全球共情指数稳定维持在83%以上。极端理性主义组织彻底转入地下,影响力日渐衰微。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将“共情教育”纳入基础课程,教授孩子如何识别情绪、表达感受、倾听他人。联合国甚至成立“心灵联结署”,专门协调跨国共情资源分配。
然而,新的挑战也在浮现。一些心理学家警告:“过度共情可能导致边界模糊,个体丧失自我。”个别案例显示,部分“共鸣世代”儿童因频繁接收他人情绪而出现精神疲劳,甚至产生身份混淆。为此,七位守门人召开首次全球连线会议,讨论是否应设置“共情阈值”。
会议上,美?提出建议:“不如教他们区分‘感受’与‘承担’。我们可以感知别人的痛,但不必替他们背负。”
萨米尔补充:“就像雨水打湿衣服,不代表我们必须淋雨生病。”
最终决定:开发一套“情绪滤网”系统,帮助使用者建立心理屏障,既能保持连接,又不至于淹没。
系统上线当日,全球百万用户同步更新。而在后台日志中,技术人员发现一段异常记录:
>**触发条件:用户首次启用滤网**
>**反馈内容:一声轻笑,伴随一句低语??“长大了。”**
没人知道是谁留下的,但所有人都觉得,那语气熟悉得令人心颤。
春天来临时,中国西南那所小学举办了一场特别活动。学生们要用绘画表达“什么是共情”。大多数画的是牵手、拥抱、雨中撑伞,唯独那个曾躲在角落的男孩,画了一扇门。门紧闭着,门外站着许多人,手里拿着蜡烛、鲜花、信纸,却没有一个人敲门。只有一个小女孩踮起脚尖,把耳朵贴在门上,似乎在倾听里面的声音。
老师问他:“为什么这么画?”
男孩低头说:“有时候,最难的不是打开门,是让人愿意听你说。”
教室安静了很久。最后,老师把他的话写在黑板上:
>**“倾听,是最沉默的拥抱。”**
那天傍晚,夕阳洒满操场,风吹动树叶沙沙作响。远处playground的笑声依旧清脆。而在无人注意的角落,一块不起眼的石头微微发烫,仿佛刚刚被人长久握过。
风再次吹起,穿过山谷,掠过城市,拂过海洋,带着无数未说完的话、未流尽的泪、未道出的感谢,飞向下一个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