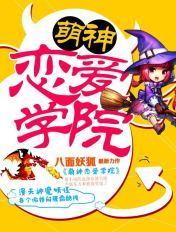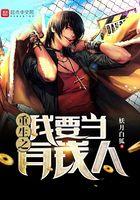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刚想艺考你说我跑了半辈子龙套? > 第495章 这就是第一人的地位(第2页)
第495章 这就是第一人的地位(第2页)
“谢谢你让我多走了十年。”
“你说‘走得稳’,我现在走路都不怕摔了。”
“我没见过你,但我相信这世上真的有好人。”
风吹起横幅的一角,上面写着七个字:“致未曾被记住的你”。
结束后,林默将这场仪式剪成短片,命名为《补丁》。发布当晚,播放量突破百万。有网友自发发起募捐,提议在原址立一块纪念牌;也有公益组织联系他们,希望能建立“普通人记忆库”,收集更多类似故事。
但更大的波澜也随之而来。
一家权威文化评论公众号发表长文,标题赫然写着:《警惕“苦难浪漫化”陷阱:当纪实沦为情绪消费》。文中指责林默团队“刻意挖掘社会边缘人物的伤痛经历,以真实之名行煽情之实”,并质问:“我们究竟是在尊重平凡,还是在利用平凡博取关注?”
文章迅速发酵,舆论分裂。支持者认为这是对底层尊严的唤醒,反对者则称其为“悲情营销”。甚至连一些曾经合作过的纪录片导演也私下劝他:“适可而止吧,别把自己搭进去。”
林默没有回应任何争议。他只是在一个雨夜,独自去了母亲的墓园。
雨水顺着伞沿滴落,打湿了他的裤脚。他站在墓碑前,轻声说:“妈,你说我是不是太固执了?明明知道这些事没人真正在乎,可我还是想做。”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可每次看到他们的眼睛亮起来,我就觉得……哪怕只有一个人被看见,也值得。”
回到家已是凌晨。他打开邮箱,发现一封陌生来信,发件人署名“王远”,正是那位职高语文老师。
>“林老师:
>
>我看了《补丁》,哭了很久。我想起父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书有人读,才算活着;人有人记,才算没死。’
>
>昨天我带学生做了一堂特别课。我让他们写下自己家里最不起眼却最重要的人??结果八十个孩子,六十多个写了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他们写的不是伟业,而是清晨一碗热粥、深夜掖被角、下雨天在校门口等的身影。
>
>我把作业整理成册,取名叫《微光集》。如果您愿意,我想把这些故事也加入您的‘未完成’计划。”
>
>??王远
林默读完,久久不能言语。他回信写道:“欢迎加入。这不是我的计划,是我们共同的寻找。”
几天后,他接到教育局工作人员电话,说是收到多所学校申请,希望将《普通人档案》系列引入校园作为生命教育课程素材。他答应了,并提出一个建议:“请让每个学生回家采访一位长辈,用五分钟视频记录他们的日常。不求精美,只求真实。”
项目启动那天,工作室挤满了前来学习拍摄技巧的学生志愿者。林默站在讲台上,放出了第一段教学片??不是技巧讲解,而是赵德海看着自己扫地画面时说的那句:“原来我也曾这么认真地活过。”
“你们要学会的,不是怎么构图、打光,”他说,“而是怎么放下预设,真正去看一个人。当我们不再急于定义他人,才能听见他们内心的声音。”
课程结束时,一个小女孩举手提问:“林老师,如果我拍的只是奶奶做饭、喂猫、晒被子,这样的片子也能算作品吗?”
林默笑了:“当然能。因为那是她的全部人生。”
当晚,他又梦见了母亲。这一次,她不再是行走于走廊的幻影,而是坐在一间教室里,周围坐满了孩子。她正指着投影幕布,上面播放的是学生们提交的“五分钟家史”视频。画面中,一位白发老人默默擦拭亡妻遗照;一个农民工父亲在工棚里给女儿读信;一位环卫阿姨下班后去菜市场买鱼,只为满足孙女“今晚想吃清蒸”的小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