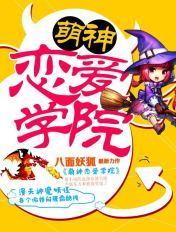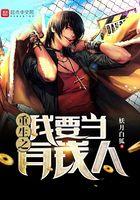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刚想艺考你说我跑了半辈子龙套? > 第495章 这就是第一人的地位(第1页)
第495章 这就是第一人的地位(第1页)
第497章让人羡慕的待遇!
郭帆的话其实并没有多少毛病。
别看奥斯卡嘴上说的什么公平公正,但是别说电影圈里面的人了,哪怕就是外面的网友、路人都知道其中其中各种弯弯绕绕。
更别说奥斯卡。。。
林默把《底片人生》的第三章保存后,没有关机。他点开一个名为“未完成的故事”的文件夹,里面已经存了十几个视频片段,每一个都标注着简单的人名和日期:王远、赵德海、老周修鞋摊……还有几个是空白的,只写着“待访”二字。他双击打开最新的一段录音??那是昨天在福利院门口,小舟父亲突然指着一辆三轮车说:“这车铃……声音很熟。”他的声音干涩却清晰,像从一口深井里打上来的水,带着久违的温度。
林默当时立刻掏出手机录了下来。那辆三轮车上堆满了旧书报,车主是个收废品的老汉,穿着洗得发白的军绿外套,脚边放着一只铁皮桶,上面用红漆歪歪扭扭写着“李记回收”。老人听见铃声回头,看见他们举着机器,皱眉道:“拍啥?我又不是景点。”
“您认识一个叫老周的修鞋匠吗?”小舟鼓起勇气问。
老人愣了一下,眼神忽然变得遥远。“老周?城北槐树巷那个?早没了。前年冬天冻死在桥洞下,没人知道名字,殡仪馆按无主尸处理了。”他说完叹了口气,“他以前常拿旧鞋换我这里的报纸看,说是爱读武侠小说……我说你扫地不如练剑,他还真比划过两下。”
风忽然大了起来,吹得三轮车上的塑料布哗啦作响。小舟站在原地没动,手指紧紧攥着摄像机带子。她想起父亲说过的话??“人心也要常修补”,而如今,那个说这话的人早已不在人世,连一块墓碑都没留下。
林默按下录制键,镜头对准那辆三轮车。铁皮桶边缘有一道裂口,被胶带缠了好几圈;车把上挂着半截手套,线头松散,像是手工织的。他蹲下来,发现车座底下压着一本破旧的《射雕英雄传》,封面脱落,页角卷曲,内页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两个男人并肩站着,一人拎着工具箱,一人推着三轮车,笑得坦荡。
照片背面写着:“兄弟俩,一修鞋一收破烂,1998。5。1槐树巷口留念。”
林默把这张照片扫描进电脑时,天已经黑了。他在搜索框输入“老周修鞋槐树巷”,跳出的信息寥寥无几,只有一条本地论坛十年前的帖子:“求助:有没有人记得城北有个独腿修鞋师傅?我妈临终前一直念叨要还他五块钱。”发帖时间是2013年,无人回复。
他拨通阿阮电话:“你能联系社区档案室吗?查查当年拆迁名单里有没有姓周的残疾人。”
第二天中午,消息回来了。档案显示,2001年槐树巷改造时,确实有一位名叫周文斌的残疾居民拒绝搬迁,后因火灾导致房屋倒塌,本人失踪,列为“下落不明”。备注栏写着一句轻描淡写的话:“疑似精神障碍,长期独居。”
林默盯着屏幕,胸口像被人狠狠捶了一拳。他知道,在那些被简化为表格与数字的记录背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如何一点点被世界抹去的过程。没有追悼会,没有讣告,甚至连死亡都无法确认??仿佛他从未存在过。
但他存在过。
就在当天下午,他们再次出发。这次的目的地是城东垃圾中转站,据李姓老人说,他现在偶尔还会去那里分拣可回收物。路上,大川翻看着手机资料,忽然抬头:“你们知道吗?国内每年有超过四万名‘三无’逝者??无名、无主、无亲属认领。他们的骨灰通常存放三年,到期就统一火化撒入江河。”
“我们能不能……为老周做点什么?”阿阮低声问。
林默沉默片刻,说:“我们可以为他办一场告别仪式。哪怕没人来,我们也得让他正式地走一次。”
他们在中转站找到了李师傅。听说他们的来意,老人摘下帽子擦了擦汗,眼眶红了:“老周啊……他是苦命人。老婆跟人跑了,儿子高烧没及时治,脑子坏了,十二岁那年掉进河里……他从此就不说话了,只会修鞋。可你知道最怪的是啥?他每双修好的鞋,都要塞张小纸条进去,写‘愿你走得稳’。”
“他还给别人希望?”小舟怔住。
“是啊。”李师傅点头,“他说,脚踩在地上的人,才有资格做梦。”
林默当即决定,要在原槐树巷旧址举行一场“记忆归还”行动。他们打印出老周的照片、手绘了他的生平时间线,还根据李师傅的回忆,复刻了一张修鞋摊的模型??木凳、工具箱、补丁摞补丁的遮阳伞。小舟的父亲全程参与布置,甚至主动拿起锤子钉架子,动作缓慢却坚定。当他把最后一颗钉子敲进去时,忽然喃喃道:“我记得……他给我的鞋补过三次。”
那一刻,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事。
这是三年来,他第一次说出完整的往事。
仪式当天,来了十几个人。有当年住在槐树巷的老邻居,有曾被老周免费修过鞋的年轻人,还有一个拄拐杖的老太太,颤巍巍递上一双童鞋:“这是我孙子小时候穿的,老周修过。我一直留着,就想等有一天能当面谢谢他。”
林默架起摄像机,没有剪辑,全程直播。镜头扫过那张空着的修鞋凳,扫过墙上贴满的便签纸??上面写满了陌生人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