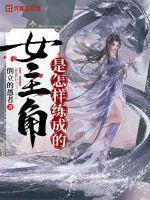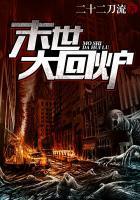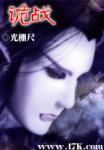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刚想艺考你说我跑了半辈子龙套? > 第494章 回国再遇郭忛(第3页)
第494章 回国再遇郭忛(第3页)
良久,赵德海抬起头,点了点头。
拍摄很简单。他像往常一样清扫院子,动作缓慢却一丝不苟。镜头静静跟着他,记录下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记录下他弯腰捡起一片落叶的瞬间,记录下他停下脚步,望着天空喃喃一句:“今天风不大,适合晒被子。”
结束后,老人问:“我能看看吗?”
他们当场用笔记本电脑播放。赵德海看得极慢,一遍又一遍回放自己扫地的画面,忽然笑了:“原来……我走路还挺稳的。”
小舟在一旁忍不住问:“赵爷爷,您有没有遗憾?”
老人想了想,说:“有啊。我儿子小时候想学钢琴,可我没钱买琴,也没文化教他。后来他去了南方打工,再没回来。”
他顿了顿,“要是当初我能多挣点钱,或许他就不会走。”
林默沉默片刻,低声问:“您还记得他喜欢哪首曲子吗?”
“《梦中的婚礼》。”老人说,“他说听起来像雪落在屋顶上。”
当晚,林默联系了一位音乐人朋友,请他用电子合成器还原这首曲子,并配上赵德海扫地的节奏作为背景音轨。几天后,他们带着便携音箱重返福利院。
当旋律响起时,老人愣住了。他听着听着,竟随着节拍轻轻晃动身体,嘴里哼了起来。
那一刻,扫帚成了指挥棒,院子成了音乐厅,而他,终于成了主角。
影片完成后,林默将它命名为《扫地人华尔兹》,并上传至平台。他在简介中写道:
>“献给所有在生活边缘起舞的人。你们或许从未站上舞台,但你们的脚步,早已谱成了大地的乐章。”
评论区很快被点亮:
“我爸爸也是环卫工,他从不说苦,只说‘城市干净了,人心才不会脏’。”
“昨天我妈去世了,我在她枕头下发现一张纸条:‘希望我走后,有人帮我把阳台的花浇了。’??原来她到最后,还在替别人着想。”
“我一直觉得自己太平凡。可看完这个,我想通了:平凡不是缺陷,是沉默的勇敢。”
风波再次袭来。某主流电视台发布专题报道,称此类作品“过度美化苦难”“煽情成瘾”“缺乏审美高度”。节目嘉宾语重心长地说:“艺术应当引领大众向上,而不是拉着他们沉溺于琐碎。”
林默没有回应。他只是在课堂上放了一段新的开场视频??是赵德海看完成片后的反应。老人反复看着自己扫地的身影,最后轻声说了一句:“原来我也曾这么认真地活过。”
“你们觉得,这是煽情吗?”林默问学生们。
大川摇头:“这不是煽情,是正名。他一辈子被人忽略,现在终于被人看见了。”
林默点头:“对。我们不是在制造悲情,是在归还尊严。”
一个月后,《扫地人华尔兹》被法国一家小型电影节选中参展。主办方来信说:“您的作品让我们想起罗伊?安德森的哲学??在荒诞中寻找诗意。但您更进一步:您在尘埃中发现了神性。”
林默把这封信打印出来,贴在工作室的墙上。下面压着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她站在文化馆门口,笑容灿烂,手中举着一台老式摄影机。
那天夜里,他又梦见了母亲。梦里她穿着八十年代的蓝布衫,走在一条长长的走廊上,两侧挂满了放映中的画面??有阿阮的母亲缝衬衫,有大川的师傅擦消防栓,有小舟的父亲喊出女儿的名字,也有赵德海在音乐中扫地……
她回头对他笑:“你看,他们都亮起来了。”
醒来时,天还未亮。他起身走到窗前,看见一轮残月悬于树梢,清辉洒落如霜。
他打开电脑,在《底片人生》第三章写下:
>“有人说,跑龙套的人注定看不见光。可我渐渐明白,正是因为我们曾在黑暗中穿行太久,才格外懂得如何为他人点灯。我不是要成为明星,我只是想让更多‘不合格’的灵魂,有机会被世界温柔凝视一次。”
晨光渐起,梧桐树影缓缓移动,像时光的手指轻轻拨动琴弦。
他知道,这条路还很长。
但他不再急于抵达终点。
因为在沿途的每一次快门声中,他都听见了生命最真实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