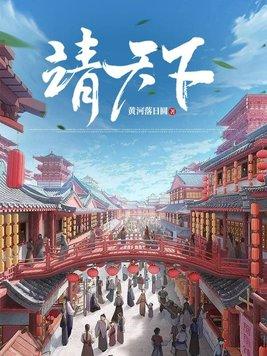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让你下山娶妻,不是让你震惊世界! > 第1654章 这都是他的基石啊(第1页)
第1654章 这都是他的基石啊(第1页)
果不其然,身后的冉茜茜率先被吵醒了。
她烦躁的翻了个身。
“谁啊,大清早的,找死了,找死啊!”
眼看着她的小粉拳就要挥到冷希的脸上了,明川赶紧抬起手轻轻握住了她的拳头。
“宝贝儿别气,你们再睡会儿,我下去看看。”
有了明川这声安抚,三个人紧皱着的眉头这才松开了一些,又舒舒服服的继续进入到梦乡了。
明川见此无奈的摇摇头,笑着起身穿好衣服下了楼。
随即,打开门,果然看见院子里站着一大群人!
为首的叶堰抚着胡须。。。。。。
雨季来得突然,像一场迟到的道歉。
江南小镇的青石板路吸饱了水汽,踩上去泛出幽暗的光。屋檐连成一片低垂的灰线,雨水顺着瓦当滴落,在巷口汇成细流,裹着几片泡发的槐花缓缓流淌。茶馆老板老吴照例清晨五点开门,扫帚刚碰地,就听见柜台上的老式收音机“咔”地响了一声??那不是电波杂音,而是一声极轻的叹息。
他停下手,盯着那台漆皮剥落的牡丹牌收音机看了许久。这机器三年没修过,电池早耗尽,天线也断了半截,按理说不可能发声。可刚才那一声,分明是他亡妻临终前在病床上说的最后一句话:“别关灯。”
老吴的手抖了。他慢慢蹲下,把耳朵贴在收音机外壳上,仿佛怕惊走什么。潮湿的空气里,隐约有布料摩擦的声音,像是有人坐在对面藤椅上轻轻晃腿。他不敢抬头,只低声问:“是你吗?”
没有回答。但收音机的旋钮自己转动了一格,调到了一个从未注册过的频率。一段旋律流淌而出??是《茉莉花》,但用的是口琴吹的,断断续续,带着孩子气的生涩。那是他们儿子八岁时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曲子,录在一盘早已遗失的磁带里。
老吴的眼泪砸在地板上。他忽然想起昨夜梦见的事:妻子站在老屋门口,手里捧着一盆铃兰,对他说:“今天我也在听。”醒来时窗台上真多了一朵不知何处飘来的铃兰花瓣,湿漉漉地贴在玻璃上,像谁留下的指纹。
他不知道的是,在千里之外的成都,一个叫周小满的女孩正坐在地铁车厢里,耳机里播放的正是这段口琴版《茉莉花》。她不知道这首曲子从何而来,只记得三天前深夜刷手机时,偶然点进一个名为“回声地图”的页面,自动推送了这段音频,标题写着:**“来自江苏宜兴,2003年儿童节,我想妈妈听见我。”**
她听得入神,指尖不自觉跟着节奏轻敲膝盖。而就在那一刻,车厢顶部通风口的金属叶片微微震颤,发出与口琴声完全同步的嗡鸣。邻座一位闭目养神的老太太突然睁开眼,喃喃道:“这调子……是我孙子小时候最爱吹的。”
周小满转头看她,老太太却已重新合眼,嘴角浮起一丝笑。列车驶过隧道,黑暗吞没一切,耳机里的音乐却愈发清晰,甚至夹杂进一声稚嫩的欢呼:“奶奶!我吹得好听吗?”
她猛地摘下耳机,心跳如鼓。可周围乘客毫无反应,仿佛只有她听见了那声音。她颤抖着手打开“回声地图”,想留言询问来源,却发现评论区早已被清空,只剩一行系统提示:
>“该录音已被共感网络回收,感谢您成为传递者。”
她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直到当晚回家,发现阳台上那株枯死两年的绿萝竟抽出新芽,叶脉中流动着微弱金光。她伸手触碰,整片叶子忽然震动起来,播放出一段陌生男声的独白:
“如果你听到这个,请告诉林素琴老师,她的学生陈默……没有忘记她。”
周小满怔住。林素琴?这不是前几天新闻里那位因“铃兰奇迹”而广为人知的上海老人吗?她立刻上网搜索,才得知林素琴的女儿已于去年冬天去世,消息封锁已久。而那句“妈,冷”,成了母女间最后的对话。
她盯着那段语音反复听了十几遍,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新闻报道中留下的社区电话。接电话的是位社工,语气疲惫:“林老师最近精神不太好,总说女儿还在加拿大,每天对着花盆说话……你要不要来见见她?”
第二天下午,周小满提着一盆新开花的铃兰来到养老院。推门进去时,老人正坐在轮椅上,望着窗外发呆。听见脚步声,她缓缓回头,眼神浑浊却温柔。
“你来了。”她说,像是等了很久。
周小满愣住:“您认识我?”
“不认识。”老人摇头,“但我听见你走路的声音里有风的味道,还有……一点口琴的余音。”
她把绿萝录音放给她听。林素琴听完,久久未语。然后她抬起手,轻轻抚摸那盆铃兰的花瓣,低声道:“陈默是我班上最安静的孩子,上课从不举手,作文却写得像诗。后来他退学了,听说去了山区支教……再也没消息。”
她顿了顿,眼中泛起水光:“如果他还活着,应该也会希望我知道吧。”
话音落下,窗外骤然刮起一阵风,掀动窗帘,铃兰花瓣簌簌抖动。一滴露珠坠下,在地板上划出短短一道痕迹,形状竟酷似一个汉字:“信”。
周小满屏息凝视。她忽然意识到,这不是巧合。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经历类似的“回应”??不是语言,不是影像,而是以气味、温度、震动、光影的方式,完成那些未能出口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