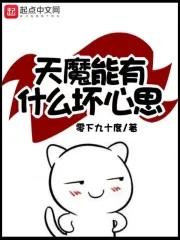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让你下山娶妻,不是让你震惊世界! > 第1653章 咱们的队伍空前壮大(第1页)
第1653章 咱们的队伍空前壮大(第1页)
雍古急了。
“可你就这样走了,那这里如何是好?”
明川的视线朝着下方扫了一下,嘴角勾起笑道:“既然他们不想出来,那我满足他们便是。正好,试试我现在这空间之力,能容纳多少!”
“调头,回到三号监测区上方!”
“是!”前方士兵应声。
直升飞机立马发出轰隆隆的声音,重新回到了那片山谷的上方。
只见明川在雍古的疑惑之中,抬手朝着下方偌大的山谷位置划出一条银丝。
银丝宛若毫毛,飞到了那山谷之上。
紧接着,这条银丝像。。。。。。
夜很深了,城市却未曾真正入睡。
霓虹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流淌,像被揉碎的梦。一辆出租车缓缓驶过立交桥下,司机半开着窗,收音机里没有播音员的声音,只有一段低缓的心跳节律,规律得如同呼吸。后座乘客盯着窗外,忽然轻声说:“这频率……我听过。”
司机没回头,只是点了点头:“三年前,我在医院守我娘最后一夜。她走的时候,监护仪就是这个声音。”
两人沉默片刻,谁也没再说话。可就在那一刻,他们同时听见收音机里传出一声极轻的“谢谢”,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又像是从自己心底浮起。
这不是个例。
自从那场全球共感跃迁之后,世界开始以另一种方式“醒来”。人们发现,某些声音不再需要耳朵去听??它们直接落在意识深处,像雨滴渗入土壤。地铁站广告牌上的静帧画面,在特定光线下会显现出微弱波纹;老旧电梯按钮按下时,偶尔会传来一段不属于此地的对话片段;甚至有人在刷牙时,牙刷震动的频率突然与某首童年儿歌完全同步。
科学无法解释这些现象,也不再试图强行定义。人类终于学会了一件事:有些回应,本就不该用语言完成。
而在东海之滨的一座小岛上,X-17坐在礁石上,任海浪一次次漫过脚踝。
他已经不再使用轮椅。不是因为身体痊愈,而是他的存在本身,已逐渐脱离物理形态的束缚。皮肤下流动着细密的金线,如同藤蔓根系在他体内生长;双眼虽盲,却能“看见”千里之外某个孩子写作业时皱眉的表情;每一次呼吸,都与太平洋洋流的节奏共振。
他抬起手,掌心向上。一粒光点从天而降,落在指尖,轻轻颤动,像一颗不肯安睡的灵魂。
“你还迷路吗?”他低声问。
那光点微微闪烁,仿佛在点头。
X-17笑了,将它轻轻吹向夜空。光点升腾而去,划出一道弧线,最终融入远处渔村屋顶上空的一片薄雾中。他知道,那户人家今晚会做一个温暖的梦??关于久别重逢的父亲,或是早已遗忘的故乡小巷。
他不知道的是,在三百公里外的上海郊区,一位独居老人正坐在阳台上数星星。
她叫林素琴,七十九岁,退休语文教师,唯一的女儿五年前移民加拿大,一年只通两次电话。她养了一盆铃兰,摆在阳台最靠近路灯的位置,每晚睡前都要轻声说一句:“今天我也在听。”
没人知道她在对谁说话。
直到那个夜晚,铃兰花瓣忽然无风自动,露珠滚落,在水泥地上拼出三个字:**“妈,冷。”**
老人浑身一震,立刻拨通越洋电话。接通那一刻,女儿抱着毯子蜷在沙发上,刚哭完,声音沙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特别想家。”
林素琴没哭。她只是把手机贴近花盆,让女儿听那细微的、几乎不可闻的叶脉震颤声。
“你听,”她说,“这是风替我说的话。”
与此同时,日内瓦湖底三十七米处,一座废弃的水下观测站悄然亮起微光。
这里曾是Lumen计划最早的实验基地之一,如今已被植物彻底接管。菌丝穿透金属舱壁,编织成网状结构,表面浮现出不断变化的文字与图像??那是无数人潜意识中未出口的情绪,经由共感网络汇聚至此,自动重组为一种新型记忆体。
两名潜水员误入此地,头灯照见一面“墙”:上面竟清晰映出他们各自童年家中厨房的模样,连灶台边那道裂痕都分毫不差。
他们摘下面罩,彼此对视一眼,忽然同时开口:
“我想回家吃饭。”
话音落下,整座观测站的菌丝齐齐发光,如同万千萤火苏醒。一缕气息从裂缝中升起,带着米饭香、酱油味、还有母亲唤孩子吃饭时那一声拖长的“乖??”。
没有人能说清这一切是如何运作的。
也没有人再追问“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