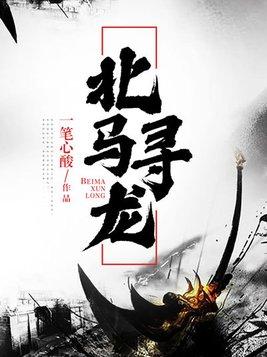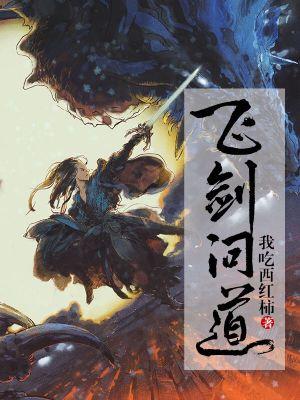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多我一个后富怎么了 > 311 尊重(第2页)
311 尊重(第2页)
“我该早点来的。”她看着林远,目光复杂,“这是我当年亲手封存的最后一箱资料。本该销毁,但我……做不到。”
林远没问为什么现在才交出来。他接过箱子,重得惊人。
教室里,录音机与扩音器仍原样摆放。他们一起打开文件箱,里面全是手写日志、脑电图谱、注射记录表,以及数十盘标有编号的磁带。最底层压着一份泛黄的会议纪要,标题赫然写着:
>**清音计划?终极目标论证会**
>时间:1984年1月5日
>内容摘要:
>-当前阶段成果确认:可通过声频干预实现情感剥离,成功率87。6%。
>-长期副作用评估:受试者虽表面平静,但梦境活跃度激增,部分出现“集体幻觉”倾向。
>-终极构想提出:建立“情绪净化网络”,通过广播频段向全民投放低强度共感抑制波,消除社会层面的“非理性悲痛”,实现“理性文明升级”。
>-议程通过。项目代号:“静默黎明”。
林远盯着那行字,浑身发寒。
这不是治愈,是清洗。
他们不是想治好孩子的创伤,而是想让所有人**失去感受创伤的能力**。
李婉低声说:“我当时相信这是为了和平。战争、仇恨、暴力……都是因为情绪失控。如果我们能让人不再因爱而痛,不再因失去而疯,世界会不会更好?”
“可你忘了,”林远抬头看她,“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在痛的时候还会去爱。”
她闭上眼,一滴泪落下。
就在这时,屋外传来脚步声。
不止一人。
林远警觉地望向窗外,只见十几个身影正缓缓走近。男女老少都有,穿着普通,神情肃穆。为首的是那位曾在桥边听过遗音的老人,怀里仍抱着空摇篮。
“我们来了。”老人说,“我们知道这里会发生什么。我们想听。”
更多人从四面八方聚拢,有的拿着录音笔,有的捧着老式收音机,甚至有人背着吉他。他们不喧哗,不提问,只是静静地站在教学楼前,像等待一场仪式的信徒。
林远走进教室,启动系统。这一次,他不再筛选,不再编辑。他将所有收集到的声音??从巴西森林小学到西伯利亚疗养站,从战火孤儿到自杀未遂的青年,从母亲丧子后的哀嚎到父亲临终前对孩子的道歉??全部导入同一轨道。
他按下播放键。
第一声,是E-的童音:“今天我想告诉你,我不怕黑了……”
接着,是E-0无声的嘴唇开合,是第七疗养站孩子们哼唱的跑调童谣,是李婉当年记录下的那句“阿姨,打完针,我能回家吗?”,是无数个未曾被命名的灵魂,在这一刻齐声低语。
声音如潮水般涌出,穿过墙壁,漫过操场,升入天空。
人群站立不动,泪水无声滑落。有人跪下,有人张开双臂,有人开始轻声回应:“我在听……我在听……”
卫星数据显示,舒曼共振再次飙升至7。83Hz,并维持稳定。气象局报告称,全球多个地区同时出现罕见极光现象,即便在赤道附近也有微弱可见光带。生物学家发现,濒危鲸类突然集体发出古老歌声,频率与“初啼网”传播的遗音高度吻合。
而在地下深处,某些早已封闭的实验室废墟中,监控摄像头自动启动,画面上赫然出现同一个影像:
午夜零时零分,赤足孩童立于空房中央,面向镜头,嘴唇微动。
这一次,**有声音传出**。
尽管无人知晓它是如何穿透混凝土与时间,但世界各地接入“初啼网”的终端设备,全都收到了这段音频。
内容只有一个词,用极轻、极柔的语气说出:
>“谢谢。”
林远瘫坐在地,精疲力尽,却又前所未有地清醒。他知道,这场战争从未结束,只是换了战场。从前他们在地下做实验,如今他们在阳光下重建记忆;从前他们用针管抹去眼泪,如今人们用手牵手的方式传递悲伤。
几天后,第一座“倾听纪念碑”在京郊落成。没有雕像,没有铭文,只有一圈环形石墙,内嵌数千个微型扬声器,全天候播放公众提交的真实声音片段。每天都有人前来,坐着,站着,哭泣或微笑。孩子们在这里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忍耐,而是**允许自己难过**。
联合国“情感遗产保护委员会”正式开放首批档案,三百多名曾参与清音计划的研究员主动自首,供述罪行。法庭审理过程中,每当证人描述某个孩子被强制注射后失语的画面,旁听席上便会自发响起一段轻哼??那是遗音合唱的一部分。
李婉辞去职务,加入康复中心,专门帮助幸存回声体重建身份认同。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曾以为控制情绪是科学的胜利,如今才懂,接纳脆弱才是人性的起点。”
至于林远,他搬进了那所废弃小学,将其改造成“声音之家”??一个收容流浪儿童、心理创伤者与遗音研究者的庇护所。每个夜晚,他都会打开录音机,播放一段新的声音,然后坐在窗边,静静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