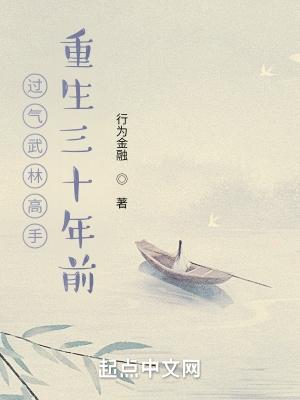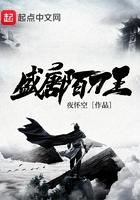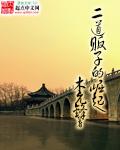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从离婚开始的文娱 > 第一千四百四十三章(第2页)
第一千四百四十三章(第2页)
他忽然明白了父亲为何从未回家。不是不想,而是不能。一旦回来,就会说出真相;一旦开口,就会牵连太多人。所以他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消失,选择用自己的死,换来系统的短暂安全。
可今天,他不能再沉默。
当晚,他将日记本扫描存档,加密上传至“遗声计划”的核心数据库,并在官网首页新增了一个红色按钮:“**听见?1967**”。点击后,自动播放一段AI还原的父亲声音,朗读那句最后的留言。
不到两个小时,访问量突破十万。微博再次炸锅,#听见1967#冲上热搜榜首。无数网友留言:
>“我爸也是这样的人,一辈子憋着不说。”
>“我们欠这些人的,不只是道歉,是正名。”
>“请把这本书出版,我要买十本。”
凌晨两点,林晚轻轻推开门,看见他还坐在电脑前,双眼通红。
“你还记得我们离婚时你说的话吗?”她轻声问。
“哪一句?”
“你说,‘我只想写点让人开心的东西’。”
他笑了:“现在我还是这么想。只不过,让人开心的前提,是先让人能说话。”
她走到他身后,轻轻抱住他:“小月睡着前说,爷爷今天晚上来看她了。穿着蓝工装,笑着对她点头。”
王乐天闭上眼,喉头一紧。
他知道,这不是幻觉。是一种传承。父亲的声音,终于穿过了四十七年的风雪,抵达了下一代的梦中。
四月二十三日,王乐天启程前往攀枝花。
临行前,他把所有资料备份交给了三位不同领域的学者:一位是历史学家,一位是法学教授,一位是独立纪录片导演。每人一份,互不知情。他留下话:“如果我失联超过七十二小时,立即公开全部内容。”
飞机降落在攀枝花机场时,天空灰蒙蒙的,远处群山笼罩在云雾中。接机的是当地一位退休教师,姓陈,曾在“三线建设”时期担任宣传干事。
“你来得正是时候。”老陈握着他的手,神情凝重,“昨天,市政府贴出公告,说要拆除最后一片老职工宿舍区,建商业综合体。那些房子,住过三千多名三线工人,现在说拆就拆。”
王乐天心头一紧:“有没有抢救性记录?”
“有,但我们人手不够。而且……有人阻挠。”
果然如此。
第二天一早,他便带着团队进入即将拆迁的片区。斑驳的墙面上还留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标语,楼道里堆满废弃家具,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铁锈的气息。他们在一栋六层老楼的三单元找到了一间保存完好的房间??门锁已坏,屋内一张木床、一个五斗柜、一台老式收音机,墙上挂着全家福。
照片上是一家三口,男人穿着工装,笑容憨厚。柜子里有一本工作日志,记录着从1970年到1985年的每一天排班与检修任务。最后一页写着:
>“1985。12。17晚班,炼钢炉温异常,建议停炉检查。组长说‘赶产量’,让我别多嘴。我说了一句‘安全第一’,被记过一次。”
>“我知道他们会说我傻。可要是没人说,将来出事了,谁负责?”
王乐天翻到最后一页,发现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极小的字:
>“张建国,不是我真名。我是李长河。但我愿意替所有没名字的人叫这个名字。”
他猛地抬头,心如雷击。
原来如此。
“张建国”不是一个代号,而是一种誓约。每一个在关键时刻说出真相、却被湮灭的人,都在用自己的生命签署这份无名契约。
他们在当天下午举办了一场露天证词会,地点就在即将拆除的宿舍楼下。几十位老人拄着拐杖赶来,有人坐着轮椅,有人戴着呼吸机。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颤巍巍地拿出一张奖状:
>“这是我老伴的‘先进生产者’证书。他干了三十年,最后死于尘肺。骨灰盒上连个正式名字都没有,只写了‘攀钢退休职工’。”
王乐天接过奖状,当众念出上面的名字:**赵德全**。
然后,他在“遗声计划”的直播镜头前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将为每一位无名者正名。他们的名字,不会只刻在纸上,更要刻在土地上。”
话音未落,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现场。车门打开,下来两名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手持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