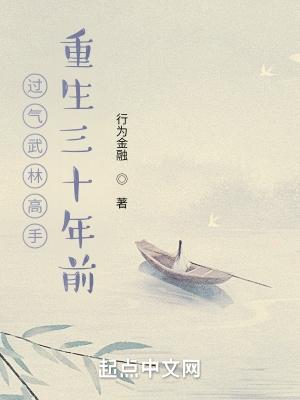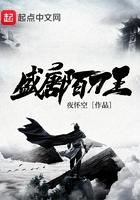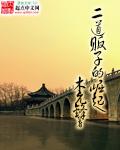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从离婚开始的文娱 > 第一千四百四十三章(第3页)
第一千四百四十三章(第3页)
“王先生,我们是市住建局的。关于您组织的这次活动,存在未经报备、煽动情绪、影响社会稳定等嫌疑,现要求立即中止。”
人群骚动起来。
王乐天没有退缩,反而走上前一步:“请问,煽动情绪的定义是什么?是老人哭诉丈夫累死在岗位上?还是孩子拿出父亲的死亡证明却得不到工伤认定?”
对方语塞。
他继续道:“你们要拆的不只是房子,是三线建设者的记忆。你们建商业体是为了发展,可发展的意义,难道不是为了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吗?”
围观群众开始鼓掌。
一名年轻记者举起手机直播,弹幕瞬间刷屏: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故事!”
>“请记住这些面孔,他们才是共和国的脊梁!”
最终,工作人员悻悻离去。
但王乐天知道,这只是开始。
当晚,他在宾馆写下新的章节:
>“他们想用推土机抹去历史,却忘了记忆长在人心深处。
>一座楼可以倒,但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它就永远立着。
>我们不是在对抗权力,我们是在唤醒良知。”
四月二十五日,他走访攀枝花钢铁厂旧址。在废弃的调度室里,他发现了一块电子屏残骸,上面竟还能显示出部分数据。经过技术修复,团队还原出一段1983年的监控录像:一群工人围在炉前,激烈争论是否停炉检修。画面中,一名工人怒吼:“温度超限了!再烧下去会炸!”
下一秒,录像中断。
而在隔壁办公室的抽屉里,他们找到一份手写报告,标题是《关于1983年8月15日重大安全隐患的紧急汇报》,落款人:**张建国(化名)**。
报告详细记录了炉体裂缝、冷却系统失效、值班干部隐瞒不报等情况。末尾写道:
>“我知道说了也没用,但我必须说。因为如果今天我不说,明天就没人替我说。”
王乐天将这份报告命名为《张建国的最后一封信》,并决定将其作为“记忆站”展馆的核心展品。
五月一日劳动节,他在攀枝花举办了第三场“无名者祭”。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特殊装置:由三百七十二块玻璃砖组成的纪念墙,每一块砖内嵌一张亲历者照片、一段语音二维码和一枚工牌复制品。人们走过时,脚下的感应灯依次亮起,仿佛踏过历史的脉搏。
当夜,央视《新闻周刊》罕见地报道了“遗声计划”,主持人在结尾说道:
>“我们常歌颂时代的飞跃,却很少追问代价由谁承担。王乐天所做的,不是揭伤疤,而是补空白。一个民族的伟大,不在于回避错误,而在于敢于直面真相。”
节目播出后,舆情骤变。曾经攻击他的公众号纷纷删文,某些部门的态度也开始松动。
五月三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动联系,表示愿协助“记忆站”项目落地,并提供部分档案支持。
同日,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回函,确认将“遗声计划”收录的三百余份口述史料纳入内部参考文献。
王乐天站在攀枝花的山坡上,望着远处初升的朝阳。山风拂过,带来铁矿石的气息。
林晚打来电话:“小月今天在学校演讲,题目是《我的爷爷是个英雄》。老师哭了。”
他笑了,眼眶却湿了。
他知道,这场战役远未结束。未来仍会有审查、有打压、有抹黑。也许有一天,网站会被关闭,展馆会被查封,书籍会被禁售。
但他不再恐惧。
因为他已明白,真正的力量,不在服务器里,不在展馆中,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里。
只要还有人愿意倾听,只要还有人敢于说出真相,那些沉默的基石,就永远不会崩塌。
而他,将继续行走在这条路上,带着父亲的日记,带着三百七十二个声音,带着无数个“张建国”的名字,走向下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