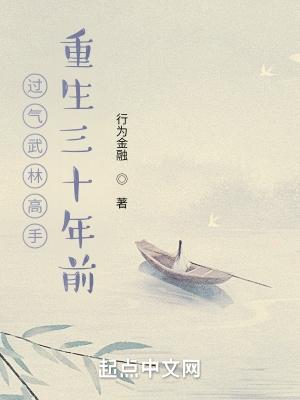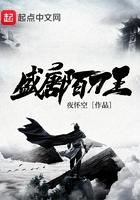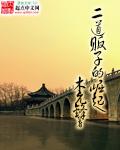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从离婚开始的文娱 > 第一千四百四十二章(第3页)
第一千四百四十二章(第3页)
四月十日,王乐天启程前往鞍山。火车穿过华北平原,驶入东北腹地。窗外景色渐变,荒地、铁轨、废弃高炉依次掠过。他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话:
>“共和国的骨骼,是由无数无名者的血肉铸成的。我们不能只赞美大厦,却遗忘地基。”
抵达当晚,他见到了曾在鞍钢保卫科工作的退休干部刘振海。老人今年八十一,精神尚可,但听力严重衰退。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老人递给他一份泛黄的名单,“这是1975年至1985年期间,因职业病死亡却未认定工伤的工人名录,共一百三十七人。当年我们偷偷抄了一份,藏在锅炉房的夹墙里,直到去年才挖出来。”
王乐天接过名单,指尖颤抖。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死因:苯中毒、矽肺、重金属肝损伤……
“我们不是不报,是不敢报。”老人哽咽,“上面说了,‘稳定压倒一切’。可我们工人,连命都不算‘一切’吗?”
第二天,王乐天走访鞍钢老厂区。在一座坍塌的焦化车间内,他发现了一块残破的荣誉榜,上面依稀可见“先进生产者”字样。他用手电照亮角落,竟看到一行刻痕:
**“张建国,1978年殉职,因通风故障吸入一氧化碳。”**
又是这个名字。
他立刻调取数据库,发现“张建国”在全国至少出现在六个不同工业城市的死亡记录中:大庆、攀枝花、玉门、洛阳、武汉、鞍山。有的是炼油工,有的是炉前工,有的是地质勘探员。年龄集中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死因多为急性中毒或突发器官衰竭,且均未被认定为工伤。
这不是巧合。这是一种系统性牺牲的标记。
他忽然明白,这些“张建国”们,或许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而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无名牺牲者的象征性名字。就像“王建国”“李建军”曾是新生儿最常见的名字一样,“张建国”也成了默默死去的工人的集体代称。
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们不需要青史留名,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国献身。可国家记住了GDP的增长,却忘了记录他们的呼吸。”
四月十五日,他在鞍山举办第二场分享会。现场来了近百人,许多人拄着拐杖,戴着呼吸机。一位老太太颤巍巍地上台,拿出丈夫的骨灰盒:“他临走前说,要是能听见有人说一声‘你没白干’,他就安心了。”
王乐天接过骨灰盒,轻轻放在讲台上,对着全场深深鞠躬:
“您没白干。你们都没白干。”
掌声雷动,泪水横流。
回到北京后,他开始撰写《沉默的基石》一书,作为“遗声计划”的阶段性总结。第一章标题是:
**“从离婚开始的文娱,到为亡者发声的使命。”**
他在开篇写道:
>“我曾以为人生的转折是婚姻的终结。后来才懂,真正的觉醒,始于对沉默的背叛。
>当我发现父亲的名字刻在荒野石碑上,而官方档案里一片空白时,我就知道??
>有些账,不能等国家来还。
>我必须成为那个持笔的人。”
四月十八日,一年前出发去大庆的日子。王乐天站在阳台上,望着远处的老梅树。花开已尽,绿叶成荫。林晚走过来,靠在他肩上。
“你还记得我们离婚那天吗?”她轻声问。
“记得。”他说,“你说我不务正业,整天写些没人看的东西。”
“现在呢?”
他笑了:“现在全世界都在看。”
她也笑了,眼里闪着光:“小月说,她长大后要当‘记忆修复师’。”
他搂住她,望着天空。
他知道,这场战役远未结束。审查、打压、抹黑可能随时降临。但他不再恐惧。
因为他已不再是那个只为娱乐大众而写作的编剧。
他是证词的搬运者,是记忆的守夜人,是无数亡魂托付声音的媒介。
而他的使命,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