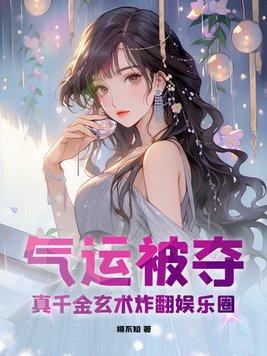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娘子天下第一 > 第六百九十七章(第1页)
第六百九十七章(第1页)
宋清他们一众人闻言,纷纷伸手端起了自己的酒杯对着柳大少回应了一下。
“三弟,干杯。”
“妹夫,干杯。”
“大帅,吾等先干为敬。”
“少爷,小的先干为敬。
柳明志嘴唇微张地。。。
夜色如墨,洒在黄土高原的沟壑之间。柳明志坐在一处废弃窑洞前的小石墩上,风从远处吹来,带着沙粒与枯草的气息。他手中捧着《承忆录》,书页微微颤动,仿佛感应到了什么。远处,几只野狗低吠着掠过山梁,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驱赶。
他刚从内蒙古归来,途中经过这片曾是陕甘宁边区的老根据地。本无意停留,可昨夜梦中,一个女人的声音反复响起:“你忘了我。”那声音不悲不怒,只是平静得令人心碎。醒来时,发现《承忆录》自动翻到了一页空白处,浮现出三个字:**李秀兰**。
这个名字不在任何已录入的档案里。
他查遍数据库,最终在一份19年地方志残卷中找到线索:李秀兰,女,二十岁,延安某医院护士,在一次敌机空袭中失踪,官方记录为“牺牲”。但民间传言不同??有人说她并未死于轰炸,而是因救治一名受伤国军士兵,被当作“通敌分子”秘密处决;更有人说,她在临刑前高喊:“我不是叛徒,我只是个医生!”
柳明志决定留下来听一听。
天还未亮,他就走访了附近几个村子。多数老人摇头不知,或避而不谈。直到中午,一位拄拐杖的老妇人将他唤进屋内,低声说:“我知道她。她是我的表姐。”
老人名叫王招娣,八十六岁,左眼失明,右耳重听。她说自己当年也在医院做杂役,亲眼看见李秀兰抱着那个伤兵躲进防空洞。“那人浑身是血,腿断了,疼得直叫娘。秀兰把他裹在白布里,自己趴在他身上挡弹片。”后来敌机走了,解放军冲进来抓人,说那伤兵是特务,而救他的人也该杀。
“他们把她拖到后山,用麻袋套头,枪都没用,怕惊动百姓。”老人颤抖着手揭开炕角一块木板,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这是她最后的样子。我偷拍的。”
照片上的李秀兰穿着洗得发白的护士服,站在一棵槐树下微笑。阳光穿过树叶落在她肩头,像一层金纱。背面写着一行小字:“愿天下无伤者。”
柳明志久久凝视,喉头哽咽。他打开录音笔,轻声问:“您想对她说什么?”
王招娣沉默良久,忽然跪倒在地,对着照片磕了一个头:“姐啊……六十年了,我一直不敢提你名字。我怕连累孩子。可现在我都快死了,不说,就真没人记得你了。”她老泪纵横,“我对不起你,没帮你收尸,没给你烧纸钱。但我每到清明,就在灶膛里烧一片纸,嘴里念你的名。我不知道你还听不听得见……但我想让你知道,还有人想着你。”
话音落下,《承忆录》忽然震动起来。紫光自封面纹路蔓延而出,照亮整个昏暗的窑洞。书页自行翻动,停在中央一页。原本空白的纸上,缓缓浮现新的文字:
>**“李秀兰,陕西绥德人,生于1927年三月初九。父亲早亡,母亲靠缝衣养家。1945年考入延安卫校,立志‘不让一人死于可治之病’。19年冬月廿三,因救治敌方士兵被定为‘思想动摇分子’,秘密处决于清凉山北麓。遗愿:若有人读到此页,请替我告诉母亲??女儿没有做错事,她只是选择了当人。”**
柳明志双手合拢,将书贴近胸口,如同怀抱一颗跳动的心脏。他知道,这一刻,死去的灵魂终于得以开口。
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正义并非总是胜利者的冠冕,有时它只是失败者眼中不肯闭合的光。我们记下这些名字,并非要翻旧账,而是要证明:哪怕在一个集体失语的时代,仍有人选择以生命说出‘不’。”
三天后,他联系上李秀兰唯一的亲人??她的外甥女,现居西安的一位退休教师。电话接通时,对方愣了很久才说话:“我妈临终前说过一句话:‘我姐姐不是坏人。’可从来没人告诉我她去哪儿了。”
柳明志把照片和《承忆录》中的文字传给她。第二天清晨收到回信,只有短短一句:“我要去清凉山,替我妈喊一声‘姐’。”
与此同时,《承忆录》云端系统再次异动。南极“悔信之林”的信号频率发生微妙变化,新增一组词汇开始循环传输:**我不是叛徒、请让我解释、我还爱着祖国、我没有武器、我不想杀人、我只是个孩子、别丢下我、你们听见了吗、我还活着吗、谁来认领我**。
国际心理学界震动。有学者指出,这十句话高度契合战乱地区平民与未成年士兵的心理创伤模式。更惊人的是,随着信号扩散,全球多个难民营报告异常现象:长期沉默的儿童开始主动绘画、书写母语诗句;一名叙利亚少女在帐篷中醒来后,用流利的阿拉伯语背诵了一段《古兰经》,而她已失语三年。
联合国紧急召开跨文明对话会议,邀请柳明志远程发言。当他出现在屏幕中,全场起立鼓掌。一位卢旺达代表含泪说道:“二十年前我亲手砍死了邻居全家,因为他们是另一个族。我以为神永远不会原谅我。但现在我知道,只要还有人愿意听,我就不是完全堕落。”
柳明志却摇头:“我不是来赦免罪恶的。我只是来确认??每一个施暴者背后,也曾是一个被恐惧撕裂的孩子。真正的宽恕,不是抹去记忆,而是看清黑暗的源头,然后选择不再制造新的黑夜。”
会后,他收到一封来自日本京都的邮件。发件人是一位百岁老人,二战期间曾在中国东北参与细菌实验研究。信中写道:“我一生未娶,独居深山。每天吃饭前都要向东方鞠躬,因为我知道盘子里的食物,沾着无辜者的血。我不求活人饶恕,只希望在我死后,能把骨灰撒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是为了赎罪,而是想离那些我伤害过的人近一点。”
柳明志回复:“您的忏悔本身就是一种偿还。我会把您的故事写进《承忆录》,让后人知道,即使最深的黑暗里,也曾有人挣扎着点亮一盏灯。”
然而,风暴也随之而来。
某夜,他在甘肃敦煌参加一场共感工作坊,刚结束分享,一辆黑色越野车疾驰而至。几名蒙面男子冲进会场,砸毁设备,撕毁参与者提交的记忆卡片,并在墙上喷出鲜红大字:“**历史属于胜利者,滚出中国!**”
警方迅速介入,嫌犯被捕。审讯显示,他们隶属于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组织,认为《承忆录》正在“瓦解民族自信”,必须摧毁。主谋是一名退伍军官,其父曾在朝鲜战场负伤,一直坚信“所有质疑战争光荣的行为都是背叛”。
消息曝光后,舆论分裂。支持者发起“万人护书行动”,自发组成志愿者巡逻队守护各地《承忆录》采集点;反对者则在网络上发起联署,要求政府取缔该项目,称其“煽动仇恨教育”。
柳明志未作回应,只是继续前行。
他来到云南怒江峡谷,拜访一位傈僳族老猎人。老人年轻时曾参与剿匪,亲手击毙一名持枪逃犯。多年后才知那人并非土匪,而是被冤枉的地主儿子,为保护家人被迫反抗。老猎人自此放下猎枪,终身素食,每逢雨夜便独自走向山林,对着空气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好人。”
录音完毕,《承忆录》再次显现异象:书中飘出一片枫叶,叶脉间浮现出一行字:“**当你杀死一个人,你也杀死了自己的一部分。唯有承认这一点,才能重新做人。**”
老人看着叶子,老泪纵横:“原来我不是疯了,我是终于被人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