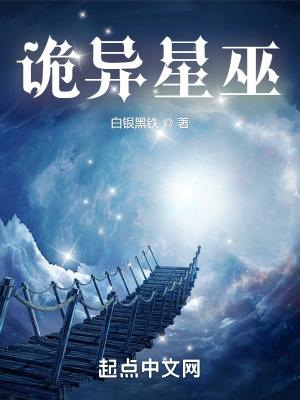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娘子天下第一 > 第六百九十六章(第1页)
第六百九十六章(第1页)
柳明志此言一出,在座的一众人纷纷神色好奇的将目光落到了宋清的身上。
“宋兄,妹夫他的问题同样也是兄弟我想要询问的问题,你与拉米尔嫂夫人昨天晚上都已经洞房花烛夜了,不知你打算什么时候安排你们两个人。。。
风从南方吹来,带着湿润的泥土气息和远处稻田的清香。柳明志背着《承忆录》穿行在云南与广西交界的群山之间,脚下的石板路早已被晨露浸得发亮,像一条蜿蜒的银线,通向云雾深处的小寨。他此行是为了探访一位年逾九旬的老妇人??据村民说,她是当年滇桂边境“血井案”中唯一活着的目击者。
山路陡峭,他的脚步却稳。一年又一年的行走已将他的身体磨成了某种工具,不是为了跋涉而跋涉,而是为了抵达那些被遗忘的角落。途中偶遇一个放牛的孩子,约莫十岁出头,赤脚踩在湿滑的石头上,眼神清亮。
“你是来找阿?奶奶的吧?”孩子忽然开口,声音脆得像山涧滴水。
柳明志一怔:“你怎么知道?”
“前天晚上,她梦见了一个穿灰布衫的人,手里抱着一本发光的书。”孩子说着,咧嘴一笑,“她说那人会来听她说话,说完就能安心走了。”
柳明志心头微震。这不是第一次有人预言他的到来。自从《承忆录》显现出异象以来,越来越多的老人、孩童甚至病危之人,会在梦中“看见”它。有人说那是亡魂引路,也有人说这是集体潜意识的觉醒。他不解释,只点头:“那你能带我去吗?”
孩子牵起牛绳,转身便走。一路上,他轻声讲述着村里的传说:那口“血井”原是一处甘泉,六十年前一夜之间变红,连续七日涌出赤水,腥气冲天。族长请来巫师作法,才知是三十具尸体埋于井底所致??皆为外乡逃荒者,因饥寒叩门求救,却被全村合谋诱杀分食。
“我阿妈说,那时候饿疯了,人不像人。”孩子语气平静,仿佛在讲一段遥远的寓言,“可阿?奶奶不肯吃,她躲在柴房哭了三天。后来每到月圆夜,她总听见井里有人敲碗,轻轻叫‘大姐,给口饭吃’……”
话音未落,前方竹林豁然开朗,一座低矮的茅屋静立山坡,屋顶飘着一缕炊烟。门口坐着一位老妇,白发如霜,双眼浑浊,手中握着一只破旧陶碗,正用指甲一遍遍刮着内壁,动作机械而执拗。
柳明志缓缓走近,蹲下身,轻声道:“阿?奶奶,我来了。”
老人手指一顿,碗落地碎裂。她抬起头,嘴角颤动:“你……终于来了。”
屋内昏暗,火塘边摆着三张小凳。柳明志取出录音笔,打开盖子,红灯亮起。老人却不急着说话,而是颤巍巍地从床底拖出一个木匣,打开后,里面是一叠泛黄的纸片,每一张都写着名字,墨迹斑驳。
“这是我记下的。”她沙哑地说,“三十一个人,一个没漏。我知道他们姓什么,从哪来,有没有爹娘……可我不敢说。我说了,村里人会杀了我。”
她顿了顿,眼泪无声滑落:“但我更怕不说。他们在我梦里排队等饭,一个个看着我,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熬不住了。”
柳明志静静听着,没有催促。他知道,有些话沉得太久,需要时间浮上来。
终于,老人抬起手,指向西墙角落的一块青砖:“那天晚上,他们被绑在柱子上,有人还抱着孩子。族长说‘活人不能饿死,死人该喂活人’。我站在人群最后,看着他们被割肉……有个女人临死前盯着我,嘴唇动了动,我没听清。第二天我去井边打水,发现她留下的银镯卡在石缝里。我偷偷捡回来,藏了六十年。”
她从颈间掏出一根麻绳,挂着一只锈迹斑斑的银镯。“我想还给她家人,可我不知道她是谁……只能每天刮这只碗,就像给她盛饭一样。我欠她的,不止一条命。”
柳明志接过银镯,触手冰凉。他轻轻放在录音笔旁,低声问:“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老人闭上眼,声音微弱却清晰:“对不起……我不是英雄,我也怕死。可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不想吃人。请你们……别恨这片土地,恨我一个就够了。”
话音落下,屋外忽起一阵风,卷起尘土,吹得竹帘狂舞。片刻后,风停,屋内温度骤降。柳明志低头一看,惊觉录音笔的指示灯由红转紫,而《承忆录》竟自行翻开,一页空白纸上浮现出一行字:
>**“陈氏玉兰,广西宾阳人,二十七岁,母亡父盲,育有一子寄养邻村。死于1963年冬月十四,因饥困求宿被杀。遗愿:望儿长大识字,勿忘母亲名。”**
柳明志浑身一震。这名字不在老人方才念的名单里,却精准对应了那个“盯着她”的女人。他抬头看向老人,发现她正死死盯着那行字,全身颤抖。
“玉兰……玉兰!”她突然嚎啕大哭,“我就知道你叫玉兰!那天你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姐姐,帮我记住名字’!我以为我忘了……原来我一直记得啊!”
她扑倒在地,额头磕向地面,一遍遍重复:“我对得起你了,我对得起你了……”
柳明志默默合上书,收起银镯与录音笔。那一夜,他在日记中写道:“记忆不是私产,它是无数亡灵托付给生者的信使。当我们拒绝倾听,便是让死者再度死亡。”
次日清晨,他将银镯的照片与老人口述上传至《承忆录》云端,并附上寻亲启事。不到四十八小时,系统自动匹配到一条信息:广西宾阳县某村档案记载,1963年确有女子陈玉兰失踪,其子后由姑母抚养成人,已于2005年病逝,但留下一女,现居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