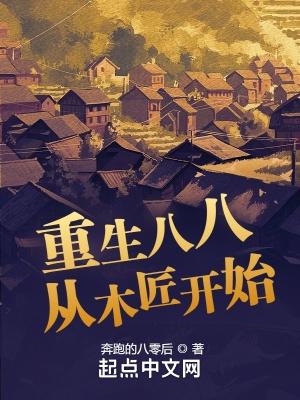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舔狗反派只想苟,女主不按套路走! > 第2009章 身份好尴尬啊(第2页)
第2009章 身份好尴尬啊(第2页)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
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
陈默和苏晚对视一眼,缓缓走向门口。
推开门的瞬间,他们愣住了。
街道上站满了人。
有纽约地铁里那位流浪歌手,怀里抱着吉他,琴弦上缠着一段蓝丝带;
有开罗集市的老陶匠,手中捧着一只铃铛瓶,瓶内黑晶碎屑微微震颤;
有西伯利亚“共鸣线”上的守夜人,肩上披着霜雪,手里提着一盏煤油灯;
还有火星基地传回影像中的李哲的女儿,如今已长大成人,手中握着一封泛黄的信,信封上写着“给爸爸的最后一句话”。
他们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着,目光齐齐望向面包店。
然后,最前面的一位老人走上前,将一块手工烘焙的吐司放在门槛上。吐司切面绘着一座小亭子,亭中两人对坐,桌上三杯热可可冒着热气。
“我来讲个故事。”老人声音沙哑,“关于我妻子临终前,梦见了一个会做星星面包的男人。”
话音落下,第二个人上前,放下一块吐司。
“我想告诉我死去的儿子,我终于学会了听他喜欢的音乐。”
第三个人,第四个人……越来越多的人走上前,每人都带着一块吐司,每块吐司上都绘着不同的画面:
一对恋人相拥,
一位母亲轻拍婴儿,
一个老人坐在长椅上看夕阳,
一群孩子手拉手奔跑在草原上……
这些画面,没有一个是伊万本人,却都与“被记住的感觉”有关。
陈默站在门内,看着这一幕,眼眶发热。
他知道,这不是祭奠,这是**回应**。
伊万曾说:“爱不会消失,它会变成风,变成光,变成你咬下一口吐司时舌尖的甜。”
而现在,全世界的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他:**我们尝到了那份甜。**
苏晚突然转身冲进店里,翻出纸笔,颤抖着写下:
>“伊万:
>今天来了很多人。
>他们都带来了故事。
>你不在,可又好像从未离开。
>如果你能听见,请告诉我们,你还好吗?”
她将纸条塞进烤箱,关上门,按下启动键。
机器嗡鸣,加热管亮起橙红光芒。
十八分钟后,烤箱“叮”地一声弹开。
吐司缓缓推出。
切面上,荧光纹路缓缓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