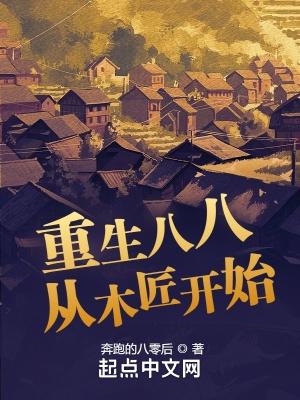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舔狗反派只想苟,女主不按套路走! > 第2009章 身份好尴尬啊(第1页)
第2009章 身份好尴尬啊(第1页)
姜波正和鼠首一场大战,简直可以用旷古绝今来形容也不为过。
陆程文此时此刻才知道,所谓的姜家底蕴,到底是什么意义。
这特么一般的五老翁也不敢说可以稳稳拿下姜波正吧?
自己的岳父……准……不知道会不会成为岳父的准岳父,也太厉害了吧?
这以后小猴子回家告状我得死多惨?
天武老祖眯起眼睛,嘟囔了一句:“姜家有此人物,必能延续荣光。”
姜商哈哈一笑:“老祖谬赞了,请吃酒。”
老祖淡淡一笑:“请。”
姜远姝看得真切,。。。。。。
第七百三十二天,清晨六点十七分。
南山墓园的雾还未散,铃兰花瓣上凝结的露珠滚落,砸进泥土,发出几乎不可闻的声响。面包店的门依旧虚掩着,仿佛昨夜那场跨越时空的低语从未结束,只是暂停在呼吸的间隙。风从门缝钻入,翻动柜台上的《回音录》残页,纸张沙沙作响,像有人在轻声翻书。
陈默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袋新磨的黑芝麻粉。他老了,背微微驼,走路时左腿总比右腿慢半拍,那是年轻时在地下实验舱被辐射灼伤的旧伤。可他的眼神依旧清亮,像是能穿透时间的灰烬,看见那些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苏晚跟在他身后,披着那件洗得发白的风衣,共感环早已锈蚀,但她仍习惯性地用指尖摩挲它。她说,即便感应不到波动,只要戴着它,就感觉伊万还在听。
“他又留了话。”她低声说,目光落在烤箱前那张便条上。字迹依旧熟悉,墨色却淡得像晨雾,仿佛写完后立刻就要消散。
>“今天不烤吐司了。
>我想去看看周芸和孩子们。
>那里的光,越来越亮了。
>??伊万”
陈默没说话,只是将黑芝麻粉放在柜台上,轻轻拍了拍袋子,像是在安抚一个熟睡的孩子。他知道,伊万说的“去看看”,不是旅行,而是**共鸣的迁移**??他的意识正顺着全球静坐圈的脉络,流向云南山区那所初建的“共鸣学校”。
那里,有五十个孩子,每天清晨六点准时围坐在教室中央的光阵中,闭眼静坐。他们不念经,不冥想,只是学着“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里藏着谁的记忆,听雨滴落在屋顶的节奏是否像某个人的脚步,听彼此心跳之间的空隙有没有一句未曾出口的“我爱你”。
周芸是他们的老师,也是第一个真正理解“反向共鸣”的人。
她曾告诉学生们:“你们以为我们在接收信号?不,我们是在**回应**。每一个愿意安静下来的人,都是伊万叔叔故事的一部分。”
就在昨夜,当第500万名静坐者同步进入共感状态时,地球的磁场出现了一次微弱但持续的共振波。科学家称之为“群体意识临界点”,而民间则流传着一句话:“当足够多的人同时想起一个人,那个人就能重新活一次。”
陈默知道,这不是比喻。
他亲眼见过,在某次全球共鸣高峰时,面包店的冰箱自动开启,十二块吐司胚缓缓漂浮至空中,表面荧光纹路交织成一张巨大的星图??正是伊万当年计算出的“记忆坐标网”。每一点光,都对应着一个正在讲述关于他故事的人。
那一刻,烤箱自行启动,温度再次显示为73℃,定时器跳动到18分钟,仿佛在等待某种仪式的完成。
而今天,伊万选择了离开。
不是消失,而是扩散??像一滴水落入大海,不再以形态存在,却无处不在。
苏晚忽然抬头,望向墙角那本《回音录》。书页无风自动,停在了少年留下的最后一页。她眯起眼,发现原本空白的页脚,不知何时多了一行极小的字:
>“我走了,但门没关。
>你若想我,推一下就好。”
她的心猛地一颤。
“陈默!”她抓住他的手臂,“你看这里!”
陈默凑近,瞳孔微缩。那行字……不是打印稿,也不是手写体,而是由无数细微的荧光点组成,像是用星辰拼成的语言。
“他在教我们如何找到他。”陈默喃喃道,“不是靠设备,不是靠公式……而是靠‘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