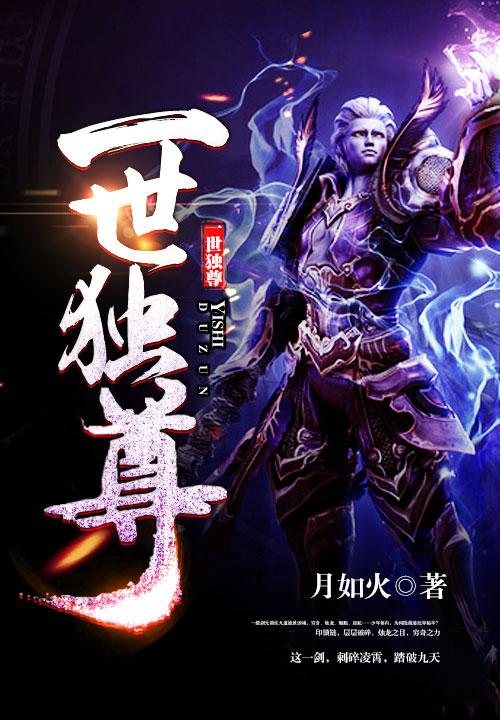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大国军垦 > 第3190章 何去何从(第3页)
第3190章 何去何从(第3页)
忽然,徽章边缘闪过一丝微光。
她屏住呼吸,看见晶体内部浮现出一行极细的字迹,像是用血写成:
>**“我不是终点,是起点。
>继续走,别停。”**
泪水滑落,她跪倒在地,对着星空大声回应:“我们还在走!我们一直都在走!”
风起了。
银草簌簌作响,万千名字在月下闪烁,宛如亿万星辰同时睁开眼睛。
三个月后,第一部《国民记忆年鉴》正式出版。扉页印着小满的照片,下方写着:
>“献给所有被抹去的人,
>和所有不肯忘记的人。”
发行当日,全国五千家书店排起长队。许多读者买书后不做阅读,而是将其供奉在家中的灵位旁,如同祭奠逝去的尊严。
而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个小镇,“拾名堂”分会迎来第一位访客??一位维吾尔族老人,拄着拐杖,背着一只破旧帆布包。他放下包,掏出厚厚一叠手写稿,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
“这是我父亲写的日记,从1949年记到1976年。他说,如果有一天中国允许讲真话,一定要把这些交给能听懂的人。”
工作人员接过稿件,翻开第一页,只见墨迹斑驳却坚定:
>“今天,我又烧掉了一本账本。他们说那是‘反动资料’。可我知道,里面记的不是政治,是我们村三百二十七口人的生死。
>我不敢刻碑,不敢立传,只能写下来,藏在墙缝里。
>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找这些名字。”
此时,距小满闭眼已过去整整一百天。
守土村举行了一场特殊的纪念仪式。没有追悼词,只有朗读声??人们轮流走上台,念出自己带来的名字,每一个音节都庄重如誓。
当最后一个名字落下,天空忽然放晴。阳光穿透云层,照在“拾名堂”屋顶的太阳能板上,反射出一道虹光,横跨整个山谷。
陈星站在人群中,仰望着那道彩虹,耳边仿佛又响起小满最后的话:
>“只要还有人愿意记住,我们就nevertrulygone。”
她摘下发间的银草花,轻轻放入门前的陶罐。罐中已积满干枯的花朵,每一片都承载着一段苏醒的记忆。
远处,新一代的孩子们正蹲在土地上,用木棍一笔一划写下两个字:
**“记得。”**
风吹过,字迹渐渐模糊,却又不断被重新书写。
如同历史本身,永不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