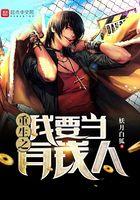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皇明 > 第409章 通商解厄宝钞重谋(第3页)
第409章 通商解厄宝钞重谋(第3页)
山东的青州、兖州两地,历来是北方养蚕的重镇,尤其是青州的柞蚕,以柞树叶为食,无需像桑蚕那样人工大规模种桑,柞树在山东的山地里随处可见,耐寒耐旱,连寒冬都冻不死。
河南东部的商丘、开封周边,也有农户养桑蚕,陕西的关中平原更是因气候温和,能种桑树,产出的蚕丝虽不如江南细腻,却也能用。
可一想到北方蚕丝的局限,朱由校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北方的蚕种,大多是柞蚕,体型比江南的桑蚕大上一圈,丝纤维也更粗、更有韧性,织出来的“鲁绸”厚实耐磨,适合做军需的帐篷、士兵的冬衣,或是北方百姓穿的粗布衣裳。
可西夷要的是细腻的生丝,用来织轻薄的丝绸,柞蚕丝显然不符合要求。
至于北方的桑蚕,只在山东临清、河南开封周边有小规模养殖。
北方的无霜期太短,一年只有一百八十到二百二十天,桑蚕一年最多只能养一两季,而江南能养三到四季。
更别说北方冬季寒冷,春季多风,桑树发芽晚,桑叶的生长期比江南短了一个月,夏季若遇干旱,桑叶减产,蚕便会断粮,产量远不及江南。
更关键的是技术差距。
江南养蚕已有千年历史,蚕农们从选种、喂叶到煮茧、缫丝,都有一套标准化的流程。
比如选蚕种要挑“白腹蚕”,喂叶要“晨采嫩桑、午采壮桑”,缫丝时要“手轻力匀”,这些都是祖辈传下来的经验。
可北方的养蚕多是农户零散经营,一户人家养个几十张蚕种,既没有统一的技术标准,也没有专业的缫丝工匠,织出来的生丝要么粗细不均,要么光泽暗沉,根本达不到西夷的要求。
“最好是压服江南,不然,就得让北方扩产了。”
朱由校喃喃自语。
山东、河南的官员此前曾上奏,说当地有不少荒地可以种桑,若是能鼓励农户“改稻为桑”,扩大桑树种植面积,再派江南的蚕农去传授技术,或许能提高北方的生丝产量。
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他便犹豫了。
“改稻为桑”听起来简单,可执行起来却容易出乱子。
若是下面的官员为了政绩,强迫农户把稻田改成桑田,不给补偿,或是勾结地主强占良田,定会激起民怨。
更别说北方百姓以稻米为主食,改种桑树后,粮食产量减少,若是遇上灾年,百姓没了口粮,怕是要闹出更大的乱子。
这一点,嘉靖年间就有了教训。
江南曾试过“改稻为桑”,结果地方官与士绅勾结,低价强买农户的稻田,逼得不少百姓家破人亡,最后还引发了民变。
如今北方的情况比江南更复杂,百姓本就贫困,若是再处理不当,怕是会重蹈覆辙。
“这事急不得啊。”朱由校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
一边是西夷订单的压力,一边是北方扩产的风险,一边还有江南士绅的阻挠,三者交织在一起,让他一时之间竟没了头绪。
他拿起案上的茶杯,抿了一口热茶,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
或许可以先派户部的官员去山东、河南实地考察,看看哪些地方适合种桑,哪些农户愿意改种,再制定详细的补偿政策。
比如种桑的农户可以免三年赋税,朝廷还提供桑苗和技术支持。
同时再加大对江南士绅的管控,让他们不敢轻易囤积蚕丝。
只是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而西夷的商船怕是等不了太久。
朱由校望着窗外渐渐升高的太阳,心中暗自盘算:
无论如何,生丝的事必须解决,这不仅关乎百万两白银,更关乎大明海贸的根基。
若是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日后如何在海上与荷兰人抗衡?
如何让大明的商船走遍四海?
思绪回转。
朱由校打开最后一封密报,紧绷的肩线终于缓缓放松。
毛文龙与天津水师昨日回到天津了。
这意味着南海的防备有了主心骨,荷兰人的觊觎、商道的安危,总算有了可托付之人。
他将密报轻轻放在一旁,指心中那点因江南士绅而起的焦躁,也消散了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