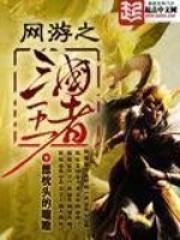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陈寅恪文集 > 第五章 新乐府(第3页)
第五章 新乐府(第3页)
华原磬云:
始知乐与时政通。
是其遣词颇相同矣。但法曲之主旨在正华声,废胡音。华原磬之主旨在崇古器,贱今乐。则截然二事也。又如华原磬五弦弹二篇,俱有慨于雅乐之不兴矣。但立部伎言太常三卿之失职,以刺雅乐之陵替。五弦弹写赵璧五弦之精妙,以慨郑声之风靡,则自不同之方面立论也。又如华原磬立部伎二篇,并于当日之司乐者有所讥刺矣。但立部伎所讥者,乃清职之乐卿。华原磬所讥者,乃愚贱之乐工。则又为各别之针对也。他若唐代之立部伎,其包括之范围极广,举凡破阵乐太平乐皆在其内,而乐天则以破阵乐既已咏之于七德舞一篇,太平乐又有西凉伎一篇专言其事,故立部伎篇中所述者,唯限于散乐,即自昔相传之百戏一类。此皆足征其经营结构,实具苦心也。
又微之所作,其语句之取材于经史者,如立部伎之用小戴乐记史记乐书,乃蛮子朝之用春秋定八年公羊传疏之例,而有:
终象由文士宪左。
及:
云蛮通好辔长駷。
等句之类,颇嫌硬涩未融。(辔长駷之辔字似即由公羊传定八年注之衔字而来。)乐天作中固无斯类,即微之晚作,亦少见此种聱牙之语。然则白诗即元诗亦李诗之改进作品。是乃比较研究所获之结论,非漫为轩轾之说也。
至于新乐府诗题之次序,李公垂原作今不可见,无从得知。微之之作与乐天之作,同一题目,而次序不同。微之诗以上阳白发人为首。上阳宫在洛阳,微之元和四年以监察御史分务东台,此诗本和公垂之作,疑是时李氏亦在东都,故于此有所感发。若果如是,则微之诗题之次序,亦即公垂之次序。惟观微之所作,排列诸题目似无系统意义之可言,而乐天之五十首则殊不然。当日乐天组织其全部结构时,心目中之次序,今日自不易推知。但就尚可见者言之,则自七德舞至海漫漫四篇,乃言玄宗以前即唐创业后至玄宗时之事。自立部伎至新丰折臂翁五篇,乃言玄宗时事。自太行路至缚戎人诸篇,乃言德宗时事。(司天台一篇,如鄙意所论,似指杜佑而言,而杜佑实亦为贞元之宰相也。)自此以下三十篇,则大率为元和时事。(其百炼镜两朱阁八骏图卖炭翁,虽似为例外,但乐天之意,或以其切于时政,而献谏于宪宗者。)其以时代为划分,颇为明显也。五十首之中,以七德舞以下四篇为一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陈述祖宗垂诫子孙之意,即新乐府总序所谓为君而作,尚不仅以其时代较前也。其以鵶九剑采诗官二篇居末者,鵶九剑乃总括前此四十八篇之作。采诗官乃标明其于乐府诗所寄之理想,皆所以结束全作,而与首篇收首尾回环救应之效者也。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是知白氏新乐府之为文学伟制,而能孤行广播于古今中外之故,亦在于是也。
元白二公作新乐府之年月,必在李公垂原作后,自无可疑。微之诗未着撰作年月,但其西凉伎云:
开远门前万里堠,今来蹙到行原州。去京五百而近何其逼,天子县内半没为荒陬。
寅恪案:旧唐书壹肆宪宗纪云:
元和三年十二月庚戌,以临泾县为行原州,命镇将郝玭为刺史。自玭镇临泾,西戎不敢犯塞。
新唐书叁柒地理志云:
原州。广德元年没吐蕃,置行原州于灵台之百里城。贞元十九年徙治平凉。元和三年又徙治临泾。
是行原州凡三徙治所。其第二次之治所为平凉县,属旧原州,据旧唐书叁捌地理志,原州中都督府在京师西北八百里。与元诗「去京五百而近」之语不合,必非所指。至行原州第一次之治所为灵台县之百里城,第三次之治所为临泾县,则皆属泾州。据旧唐书叁捌地理志,泾州在京师西北四百九十三里,与元诗「去京五百而近」之语适合。然微之诗断无远指第一次即广德元年所徙之灵台而言之理,是其所指必是元和三年十二月即第三次所徙之临泾无疑。然则微之新乐府作成之年月,亦在元和三年十二月以后,与乐天所作同为元和四年矣。此微之作诗年岁之可考者也。
乐天新乐府虽题为:
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
似其作成之年岁无他问题。然详绎之,恐五十首诗,亦非悉在元和四年所作。见下文海漫漫及杏为梁两诗笺证,兹不于此述之。盖白氏新乐府之体,以一诗表一意,述一事,五十之数,殊不为少,自宜稍积时日,多有感触,以渐补成其全数。其非一时所成,极有可能也。今严震刊白氏讽谏本新乐府序末有:
元和壬辰冬长至日左拾遗兼翰林学士白居易序。
一行。初视之殊觉不合,以元和壬辰即元和七年,是年乐天以母忧退居渭上。乐天于前二年即元和五年已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其所署官衔左拾遗,自有可议。且兼翰林学士之言,似更与唐人题衔惯例不类。(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玖本肆伍捌页岑仲勉先生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但据白氏长庆集伍叁诗解五律云:
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
可知乐天亦时改其旧作。或者此新乐府虽创作于元和四年,至于七年犹有改定之处,其「元和壬辰冬长至日」数字,乃改定后随笔所记之时日耶?否则后人传写,亦无无端增入此数字之理也。姑识于此,以待详考,并于后论海漫漫杏为梁诸篇中申其疑义焉。
关于篇章之数目,白氏之作为五十首,自无问题。元氏之作,则郭茂倩乐府诗集玖陆卷玖新乐府上载微之新乐府共十三篇,其言云:
元稹序曰,李公垂作乐府新题二十篇,稹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五而已。今所得才十二篇,又得八骏图一篇,总十三篇。
寅恪案:今元氏长庆集贰肆载新乐府共十二篇,序文亦作「十二」,适相符合,无可疑者。郭氏所见本,其「十二」之「二」,殆误作「五」,因谓其未全。又见乐天所作中有八骏图一题,而元氏长庆集叁亦有八骏图一诗,遂取之以补数。殊不知微之八骏图诗,乃五言古诗,与微之新乐府之悉为七言体者迥异,断不合混为一类。观于元氏长庆集叁拾敍诗寄乐天书云:
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诗八百余首,色类相从,共成十体,凡二十卷。
又同集伍陆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云:
予尝欲件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嬾未就。
则微之编辑自作之诗,必分别体裁,无以五七言相混淆之理。白氏长庆集之编辑,其旨亦同微之,然则郭氏编入之误,不待详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