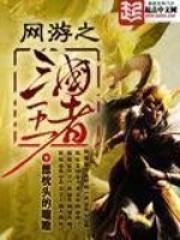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陈寅恪文集 > 第三章 连昌宫词(第4页)
第三章 连昌宫词(第4页)
其「四宗」自指肃代德顺四宗而言,所言既无譌舛,以彼例此,则应亦不致误述也。或者此诗经崔潭峻之手进御於穆宗,阉椓小人,未尝学问,习闻当日「消兵」之说,图复先朝巡幸之典,殊有契于「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之句,遂断章取义,不顾前后文意,改「五」为「六」,藉以兼指穆宗欤?此言出于臆测,别无典据,姑备一说于此,以待他日之推证可也。然其后敬宗欲幸东都,殆亦受宦官之**者,经群臣极谏,并畏藩镇称兵,不得已中止。其事本末见旧唐书壹柒拾新唐书壹柒叁裴度传,兹迻录通鉴原文及胡三省注于下,似亦与「望幸」句意关涉,读此诗者可并取以参证焉。
通鉴贰肆叁唐纪敬宗宝历二年条云:
上(敬宗)自即位以来,欲幸东都。宰相及朝臣谏者甚众,上皆不听,决意必行。已令度支员外郎卢贞,按视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宫,(胡注,自长安历华陕至洛,沿道皆有行宫。如寿安之连昌宫是也。)裴度从容言于上曰,国家本设两都,以备巡幸。自多难以来,兹事遂废。今宫阙营垒,百司廨舍,率已荒阤。陛下傥欲巡幸,宜命有司岁月间徐加完葺,然后可往。上曰,从来言事者,皆言不当往。如卿言,不往亦可。会朱克融王庭凑皆请以兵匠助修东都。三月丁亥,敕以修东都烦扰,罢之。(胡注,史言修东都之役,非以群臣论谏而罢,特畏幽镇之称兵而罢耳。)
复有传本譌写应即校改者,如「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之句,唐诗纪事本(卷贰柒)作「玄武楼前花萼废」。全唐诗本「成」字下亦有「一作前」之注,案唐六典柒云:
兴庆宫在皇城之东南,东距外郭城东垣。(原注云:即今上龙潜旧宅也。开元初以为离宫。至十四年又取永嘉胜业坊之半以置朝。自大明宫东夹罗城复道经通化门磴潜通焉。)宫之南曰通阳门,通阳之西曰花萼楼。(原注云,楼西即宁王第,故取诗人棠棣之义以名楼焉。)
宋敏求长安志陆大明宫条(参考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壹。)云:
北面一门曰玄武门。(原注云:德宗造门楼,外设两廊,持兵宿衞,谓之北衙。)
据此,玄武楼在大明宫之北面,兴庆宫远在大明宫之东南,而花萼楼又在兴庆宫之西南隅,则花萼楼准诸地望,决无在玄武楼前之理。昔人讥白香山长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之句为误,以峨嵋山在唐代嘉州境内,明皇由长安至成都不经过其下也。(见梦溪笔谈贰叁讥谑附谬误类及诗人玉屑壹壹。)殊不知微之使东川,作好时节绝句,(元氏长庆集壹柒。)亦有「身骑骢马峨嵋下,面带霜威卓氏前」之语。(并见长恨歌章。)此皆诗人泛用典故率意牵附之病,不足深责。独此诗说长安今昔之变迁,托诸往来年少之口,乃写实之词,与泛用典故者不同。其于城坊宫苑之方位,岂能颠倒错乱至此。若斯之类,自属后人传写之误。况花萼楼建于玄宗之世,为帝王友爱之美谈。玄武楼造于德宗之时,成神策宿衞之禁域。一成一废,对举竝陈。而今昔盛衰之感,不明着一字,即已在其中。若非文学之天才,焉能如是。此微之所以得称「元才子」而无愧者耶?又五代会要壹捌前代史条载贾纬之语,谓「自唐高祖至代宗,纪传已具。」则今旧唐书玄宗纪实本之旧文,夫君举必书,巡幸陪都之大典,决无漏载之理。考旧唐书玄宗自开元二十四年十月丁丑自东都还西京之后,(新唐书伍玄宗纪及通鉴贰壹肆俱作丁卯。而旧唐书捌玄宗纪作丁丑。当依张宗泰校记改为丁卯。)遂未重到洛阳。是后率以冬季十月或十一月幸华清宫,从未东出崤函一步。故通鉴贰壹肆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条(参阅新唐书伍叁食货志。)云:
先是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始用和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献策,请行籴法于关中。戊子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停今年江淮所运租。自是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癸巳敕河南河北租应输含嘉仓者皆留输本州。
国史补上略云: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时在东都,因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张曲江谏。是时李林甫初拜相,窃知上意,乃言,两京陛下东西宫也。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悦。自此驾至长安,不复东矣。
虽册寿王妃杨氏在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见通鉴贰壹肆及考异并唐大诏令集肆拾全唐文叁捌册寿王杨妃文。)其时玄宗尚在东都,未还西京。然自杨妃于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入道,即入宫之后,(详见长恨歌章辨曝书亭集伍伍书杨太真外传后。)明皇既未有巡幸洛阳之事,则太真更无以皇帝妃嫔之资格从游连昌之理,是太真始终未尝伴侍玄宗一至连昌宫也。诗中「上皇正在望仙楼,太真同凭栏干立」及「寝殿相连端正楼。太真梳洗楼上头」等句,皆傅会华清旧说,(乐史杨太真外传下云:「华清宫有端正楼,即贵妃梳洗之所。」)构成藻饰之词。才人故作狡狯之语,本不可与史家传信之文视同一例,恐读者或竟认为实有其事,特为之辨正如此。
至元氏长庆集壹柒灯影七绝云:
洛阳昼夜无车马,漫挂红纱满树头。见说平时灯影裏,玄宗潜伴太真游。
则亦微之依据世俗传说,姑妄听之,姑妄言之。既有「见说」之语,则更不足辨。而全唐诗第壹玖函张祜贰连昌宫七绝所谓「玄宗上马太真去」者,又在微之之后,尤可不论矣。又诗中「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鬭风。」之句,容斋续笔贰开元五王条已言其非事实,故兹不再辨。惟洪氏以「杨太真以[天宝]三载方入宫」,则殊疏舛,殆误会通鉴书法所致。寅恪别于长恨歌章详论之矣。更有可论者,诗云:
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
寅恪案:通鉴贰壹捌唐纪叁肆至德元载六月[安禄山]遣孙孝哲将兵入长安条考异略云:
新传又云[安]禄山至[长安],怒,大索三日。按旧传[张]通儒为西京留守编检诸书,禄山自反后未尝至长安,新传误也。
是禄山自反后未尝至长安。连昌宫为长安洛阳间之行宫,禄山既自反后未尝至长安,则当无缘经过连昌宫前之御路,故此事与杨贵妃之曾在连昌宫之端正楼上梳洗者,同出于假想虚构。宋子京为史学名家,尚有此失,特附论及之,庶读此诗者不至沿袭宋氏之误也。
此诗复有唐代当时术语须略加诠释者,如「贺老琵琶定场屋」之定,及乐府杂录敍贞元时长安东西两市互鬭声乐事中,「西市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以定东鄽之胜」之定,其义为「压」及「压场」之意也。又如「蛇出燕巢盘鬭拱」之「鬬拱」,即近日营造学者所盛称之「斗拱」。斗字义不可通,盖古代工匠用以代鬭字之简写,殊非本字。然今知此者鲜矣。(见校补记十。)
【校补记十】
(段后加:)复次,兹有一事可附论于章末者,即微之此诗与唐代久闭之离宫在寒食节时,特命中官于内斫竹之举是也。依微之此诗如「连昌宫中满宫竹」至「小年进食曾因入」一节,「初过寒食一百六,殿舍无烟宫树绿」二句,「明年十月东都破」至「不到离宫门久闭」一节,「去年??使因斫竹,偶值门开暂相逐」二句,及「自从此后还闭门,夜夜狐狸上门屋」二句等语,综合论之,则知唐代皇帝不临幸之离宫,必将宫门锁闭,而此宫门亦必尚存垣墙,否则虽闭门,亦不能阻禁外人阑入宫内也。白氏文集壹贰江南遇天宝乐叟诗云:
我自秦来君莫问,骊山渭水如荒村。新丰树老笼明月,长生殿暗锁黄昏。红叶纷纷盖欹瓦,绿苔重重封坏垣。惟有中官作宫使,每年寒食一开门。
则是乐天于元和十年贬江州司马之时,华清宫中之殿宇固甚破败,但其垣墙虽已毁损而尚存在,宫门则长闭,至寒食节始有中官开门于内斫竹也。乐天此诗乃写实之作,与微之之诗出于揣想者本自不同,然微之此诗亦依据唐代离宫一般之情况而言,绝非无中生有之描绘。如其所述久闭之离宫,尚存宫墙,在寒食节时,宫使始开门于内斫竹等事,与乐天所言华清宫之情状并无少异也。故在连昌宫词为特性之虚构,江南遇天宝乐叟诗乃通性之写实。由是而论,元白两诗可以互相证发也。
至天宝乱后,东都洛阳之上阳宫,则更有详论之必要。请略引史料,考释之于下:
杜工部集壹伍诸将五首之三云:
洛阳宫殿化为烽。
若据此语,是唐代洛阳之宫殿已于安史乱时化为烽烬矣。但检仇兆鳌杜诗详注壹陆,此句注引后汉书董卓传并曹植诗「洛阳何寂寞,宫殿尽烧焚」为释。然则仇氏仅举出少陵所用之古典,实无安史焚烧洛阳宫殿之今典。(仇氏所引子建诗乃文选贰拾曹子建送应氏诗二首之一,其诗云:「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仇氏改「宫室」为「宫殿」,意虽相同,但改曹诗以合杜句,殊可不必也。)可知子美此句乃诗人感伤之语,不可过于拘泥也。
白氏长庆集叁上阳白发人篇注云:
天宝五载已后,杨贵妃专宠后,宫人无复进幸矣。六宫有美色者,辄置别所,上阳是其一也。贞元中尚存焉。(寅恪案,鄙意以为此篇乃李绅之原唱,而元稹白居易和之者,白氏之注原出公垂也。详见此稿第伍章新乐府上阳白发人篇。)
新唐书柒柒后妃传下代宗睿真皇后传云: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吴兴人。开元末,以良家子入东宫,太子(指肃宗)以赐广平王(指代宗),实生德宗。天宝乱,贼囚后东都掖庭。王入洛,复留宫中。时方北讨,未及归长安,而河南为史思明所没,遂失后所在。代宗立,以德宗为皇太子,诏访后在亡,不能得。
通鉴贰贰陆唐纪肆贰德宗纪建中二年正月条云:
初,高力士有养女,嫠居东京,颇能言宫中事。女官李真一意其为沈太后,诣使者具言其状,上闻之惊喜。时沈氏故老已尽,无识太后者,上遣宦官宫人往验视之,年状颇同。宦官宫人不审识太后,皆言是,高氏辞称,实非太后,验视者益疑之,强迎入上阳宫。上发宫女百余人,赍乘舆服御物,就上阳宫供奉。左右诱谕百方,高氏心动,乃自言是。验视者走马入奏,上大喜。二月辛卯,上以偶日御殿,群臣皆入贺,诏有司草仪奉迎。高氏弟承悦在长安,恐不言久获罪,遽自言本末。上命力士养孙樊景超往覆视。景超见高氏居内殿,以太后自处,左右侍衞甚严。景超谓高氏曰,姑何自置身俎上。左右叱景超使下,景超抗声曰,有诏太后诈伪,左右可下。左右皆下殿。高氏乃曰,吾为人所强,非己出也。以牛车载还其家。
元氏长庆集贰肆上阳白发人篇云:
御马南奔胡马蹙,宫女三千合宫弃。宫门一闭不复开,上阳花草青苔地。月夜闲闻洛水声,秋池暗度风荷气。日日长看提象门,终身不见门前事。近年又送数人来,自言兴庆南宫至。
新唐书伍玄宗本纪(参旧唐书玖玄宗本纪下及通鉴贰贰壹唐纪叁柒肃宗纪上元元年六月条)略云:
寅恪案,代宗睿真皇后沈氏,既能于广平王即代宗收复东都之前后,皆留在上阳宫,斯为当日洛阳上阳宫非如少陵所谓「化为烽」之确证。又德宗建中二年高力士女有能以假太后之资格,居于内殿,则上阳宫之正殿,尚未被毁或被毁后重加修理之一证也。夫自天宝五载迄贞元之末,历时六十载,傥上阳宫全被焚毁,则此老宫女,岂能露宿如此之久。若谓上阳宫虽全被焚毁,后来重加修理,当修理时,将此老宫女搬移他处,迨修理完毕后,再将其迁于原处居住,则杨贵妃死已五十载,尚有何人妒忌,而令此老宫女受终身监禁之苦乎。然则上阳宫虽经安史之乱,仍未全部毁坏,故上阳白发人暂可在其中居住也。至于元微之诗云:「近年又送数人来,自言兴庆南宫至」之「近年」,其界说殊可研究。考微之此诗作于元和四年,则不能上溯至德二载玄宗自蜀郡还长安居于南内至上元元年迁于西内之时间无疑,盖历年将五十载,固不得谓之近年也。
上论洛阳宫至安史乱时迄元和初年实未毁坏并宫墙存在宫门常闭。故亦如其他唐代离宫之通例于寒食节始有中使开门斫竹之事。兹请先考唐代杏花桃花开放之时间,兼及地域并其他相关之问题,以资说明。
唐摭言叁「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条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