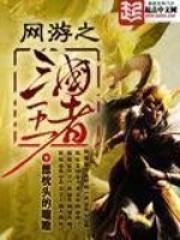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陈寅恪文集 > 第三章 连昌宫词(第3页)
第三章 连昌宫词(第3页)
[元和]末召拜膳部员外郎。
寅恪案:宪宗崩于元和十五年正月。微之于十四年已由虢州长史征还长安,为膳部员外郎,则连昌宫词之作,似即在元和十四年暮春,自通州赴虢州,就长史新任,便道经过寿安之时。元和郡县图志伍云:
河南道河南府寿安县,东北至府七十六里。
同书陆云:
河南道虢州,东至东都四百五十里。
是微之未至虢州之前,必先经东都。而东都与寿安,仅七十六里之隔,便道经行,亦颇意中之事。北地通常桃花开放之时,约值旧历清明节时。唐孟棨本事诗崔护「人面桃花」之句,为世所习知,其所谓「去年今日」即清明日也。然考是年清明在三月三日,(此系据陈垣先生中西回史日历,未知与当时实用之历如何?即使不同,要不过相差一二日,于本文论证之主旨无关也。)微之发夷陵时,已为三月十二或十三日,据通典壹捌叁州郡典壹叁云:
夷陵郡南至江陵水路二百三十七里。
江陵郡北至襄阳郡四百四十五里。
又同书壹柒柒州郡典柒云:
襄阳郡去东京八百五十七里。
今复加计自东京至寿安七十六里,共为一千六百一十五里。纵唐代里度较今略短,又微之行程较前元和十年由唐州至长安由长安至通州二役为迅速,然亦非四月初不能到寿安,是距清明已一月之久,恐不及见连昌宫墙头千叶桃落红蔌蔌之状矣。且元和十四年二月宪宗平定淄青最为当时一大事,通鉴贰肆壹唐纪宪宗纪元和十四年条(参阅旧唐书壹贰肆新唐书贰壹叁李正己传等。)云:
元和十四年二月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户部侍郎杨于陵为淄青宣抚使。己巳李师道首函至。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据此,微之即行色怱怱,所经过之大都邑如洛阳等,似不能不稍作淹留,与当地官吏及平生亲故相见,因从得知平齐消息。连昌宫词若适作于是年暮春,则虽不必如刘梦得平齐行(刘梦得文集壹伍)之夸大其事,亦不能仅敍至淮西平定而止,绝不道及淄青一字。于此转得一强有力之反证。此连昌宫词不能作于十四年暮春之证也。
总而言之,连昌宫词若为作者经过行宫感时抚事之作,则其著作之时日,用地理行程以相参校,仅有元和十年暮春及元和十四年暮春二者之可能。而元和十年微之所取之道,即韩退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之道也。故不可能。元和十四年其所取之道,即杜子美「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之道也。故似可能。但一考当年节候与花事之关系,又为不可能。二者既皆不可能,则连昌宫词非作者经过其地之作,而为依题悬拟之作,据此可以断定也。
连昌宫词既为依题悬拟之作,然则作于何时何地乎?考元氏长庆集壹贰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因有戏赠略云:
喜闻韩古调,兼爱近诗篇。好去老通川。(原注云:自谓。)
是微之在通州司马任内曾有机缘得见韩退之诗之证也。
又考韩昌黎文集拾和李司勋过连昌宫七绝云:
夹道疏槐出老根。高甍巨桷压山原。宫前遗老来相问,今是开元几叶孙。
此为退之和李正封之诗,李氏原作,今不可得见。退之作诗之时,为元和十二年冬淮西适平之后。颇疑李氏原诗或韩公和作,远道流传,至次年即十三年春间遂为微之所见,因依题悬拟,亦赋一篇。其时微之尚在通州司马任内,未出山南西道之境。观其托诸宫边遗老问对之言,以抒开元元和今昔盛衰之感,与退之绝句用意遣词尤相符会。否则微之既在通州司马任内,其居距连昌宫绝远,若非见他人作品,有所暗示,决无无端忽以连昌宫为题,而赋此长诗之理也。据旧唐书壹陆陆元稹传云:
元稹河南人,元和元年四月除右拾遗。出为河南县尉。四年奉使东蜀,使还分务东台。
夫河南虽是郡望,但洛阳则为微之仕宦居游之地。元和五年未贬江陵以前,至少亦当一度经过寿安,连昌宫门内之竹,墙头之桃,俱所目见。故依题悬拟,亦能切合。李正封之作,其艺术高下未审如何。若微之此篇之波澜壮阔,决非昌黎短句所可竝论,又不待言也。至唐诗纪事陆贰郑嵎津阳门诗,虽亦托之旅邸主翁之口,为道承平故实,抒写今昔盛衰之感。然不过填砌旧闻,祝愿颐养而已。才劣而识陋,较之近人王湘绮之圆明园词,王观堂之颐和园词,或犹有所不逮。以文学意境衡之,诚无足取。其所以至今仍视为敍述明皇太真物语之巨制者,殆由诗中子注搜采故实颇备,可供参考之资耳。
综合此诗末章前后文意言之,「官军又取淮西贼,此贼亦除天下宁」二句为已然语气,而非希望语气。故「年年耕种宫前道,今年不遣子孙耕」二句,意谓今年不依往年之例,耕种宫前御道,以待天子临幸。「今年」为淮西始平,天下遂宁之年,文意甚明。是此诗实成于元和十三年暮春。洪氏作于元和十一二年间之说,即以依题悬拟言,犹有未谛也。
连昌宫词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之语,与后来穆宗敬宗两朝之政治尤有关系,略征旧史述之于下:
旧唐书壹柒贰萧俛传(参旧唐书壹陆穆宗纪长庆元年二月乙酉马总奏条。)云:
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俛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消兵。帝既荒纵,不能深料,遂诏天下如其策行之。而藩镇之卒,合而为盗,伏于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庭凑复乱河朔,一呼而遣卒皆至。朝廷方征兵诸藩,籍既不充,寻行招募。乌合之徒,动为贼败。由是再失河朔,盖消兵之失也。
旧唐书壹陆陆元稹传云:
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新唐书壹柒肆元稹传作,长庆初潭峻方亲幸,较妥。盖新唐书壹柒玖李训传明言潭峻为元和逆党,即弑宪宗之党,而宪宗于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被弑,穆宗嗣位。次年,方改元长庆。是潭峻归朝当在长庆以前也。)出稹连昌宫词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寻知制诰。由是极承恩顾。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东节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与弘简为刎颈之交,谋乱朝政。言甚激讦。穆宗顾中外人情,乃罢稹内职,授工部侍郎。上恩顾未衰,长庆二年拜平章事。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
当宪宗之世,主持用兵者,宰相中有李吉甫武元衡裴度诸人,宦官中则有吐突承璀。然宦官亦有朋党,与士大夫相似。其弑宪宗立穆宗及杀吐突承璀之诸宦官,世号为「元和逆党」。崔潭峻者,此逆党中之一人。故「消兵」之说,为「元和逆党」及长庆初得志于朝之士大夫所主持。此事始末,非本文所能详尽。但连昌宫词末章之语,同于萧俛段文昌「消兵」之说,宜其特承穆宗知赏,而为裴晋公所甚不能堪。此则读是诗者,于知人论世之义,不可不留意及之也。
又白氏长庆集肆伍策林序略云:
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
四十四销兵数
若使逃不捕,死不填,则十年之间,十又销其三四矣。故不散弃之,则军情无怨也。不增加之,则其数自销也。
然则「销兵」之说,本为微之少日所揣摩当世之事之一。作连昌宫词时,不觉随笔及之。殊不意其竟与己身之荣辱升沈,发生如是之关系。此则当日政治之环境实为之也。
又微之赋此诗述玄宗时事托诸宫边野老之口,如「弄权宰相不记名,依稀忆得杨与李」之例,其有与史实不甚符合者,可置不论。然今日流传之本,亦有后人妄加注解者,则不得不亟为删订。如「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之句,今全唐诗本第壹伍函元稹贰肆此句下注云:
天宝十三年禄山破洛阳。
寅恪案:旧唐书玖新唐书伍玄宗纪及通鉴贰壹柒同记天宝十四载十二月丁酉安禄山陷洛阳,「十月」自是微之误记,至「十三年」之误,更不待言也。(又元氏长庆集贰肆新题乐府立部伎亦有「明年十月燕寇来,九庙千门虏尘涴」之句。)其最可异者,莫如「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之句下注云:
肃代德顺宪穆。
六字。据诗中文义,谓「今皇」平吴蜀,取淮西,(连昌宫词此数句,可与元氏长庆集贰壹代严绶谕淮西书参证。)则「今皇」自是指宪宗而言,自玄宗不到离宫之后,顺数至「今皇」即宪宗,只有五帝,何能预计穆宗或加数玄宗而成「六皇帝」?尝徧考诸本,俱作「六」,无作「五」者,可知此误字相传已久。颇疑微之于本朝君主传代之数,似不应譌误至此,而诿为野老记忆不真之言。如元氏长庆集伍贰沂国公魏博德政碑所云:
五纪四宗,容受隐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