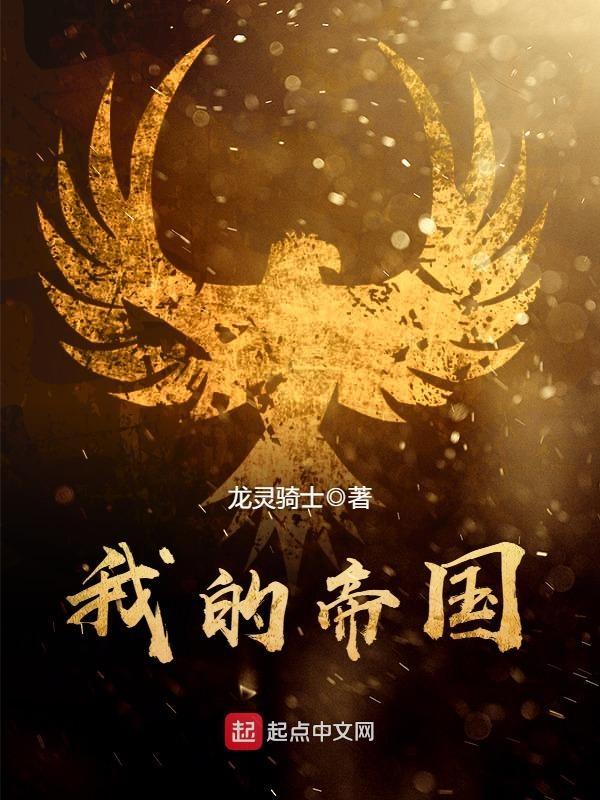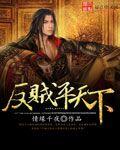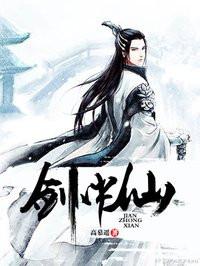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娱乐圈的老实人 > 第144章 低眉浅笑藏羞色一顾一盼自醉人23求月票(第1页)
第144章 低眉浅笑藏羞色一顾一盼自醉人23求月票(第1页)
热芭虽然不争气了点,但杨密对剧组还是挺有兴趣的。
《微微》眼看着又是一部待爆剧,这样的客串也不算浪费时间。
尤其是在看到剧组布置的婚礼现场后,杨密更是忍不住啧啧称奇。
下午,酒店宴会。。。
林晚舟没有立刻回答,只是低头看着碗里还冒着热气的汤。咸味在舌尖缓缓散开,像是某种久违的提醒??生活从不完美,但它真实地存在着。他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煮面也总放多了盐,他每次皱眉,她就笑着说:“习惯了就好。”那时他还小,不懂什么叫“习惯”,只觉得难吃。可现在想来,那碗面的味道,早已和他的记忆长在一起,分不开。
“你是不是又把盐罐子当成糖的了?”他抬眼看向程砚秋,嘴角却没忍住上扬。
她瞪他一眼,“这次可是严格按照食谱来的!不信你看手机。”说着就要去翻包。
“别查了。”他伸手拦住她,“我说刚刚好,就是刚刚好。”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眼角微微弯起,像月牙挂在初夏的夜空。她没再说什么,只是重新舀了一勺,自己尝了一口,眉头果然轻轻一皱,但很快掩饰过去,若无其事地说:“嗯,火候确实到了。”
两人之间有种默契,从来不需要戳破所有真相。就像三年前她在他最狼狈的时候出现,不是以拯救者的姿态,而是像一阵风,悄无声息地推了他一把。那时候他连门都不敢出,而她只是每天拎着饭盒敲他的房门,说:“我带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不吃的话我就坐这儿吃完再走。”他最终开了门,不是因为饿,是因为他知道,如果再不开,她真的会坐在门口等到天亮。
而现在,这种陪伴依旧安静如初。
几天后,京都国际音乐节的彩排如期进行。场馆坐落在一片湖畔高地,建筑线条极简,玻璃幕墙映着天空与湖水,仿佛悬浮于天地之间。林晚舟站在舞台中央试音时,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奇异的平衡感??脚下是坚实的地板,头顶是开阔的穹顶,耳边是熟悉的旋律,而台下,不再是嘘声、质疑或冷漠的镜头,而是一片尚未亮起却已预示光明的黑暗。
沈导在调音台前点头:“位置感不错,情绪比上次稳。记住,这不是表演,是你在说话。观众听的不是技巧,是真心。”
林晚舟闭上眼,耳机里响起前奏的钢琴声,缓慢而坚定,像一个人在深夜独行的脚步。他张开嘴,声音低沉却不怯懦:
>“我多想做个梦,梦见我仍被允许做梦……”
副歌升起,弦乐如潮水般涌来,大提琴的低鸣像一只手扶住了坠落的灵魂。那一刻,他仿佛看见了七年来每一个凌晨五点惊醒的自己:蜷缩在床上,心跳剧烈,窗外漆黑一片,世界像一座沉默的坟墓。他曾以为那一夜永远不会结束,直到今天,他终于能站在光里,把那段黑暗唱成一首歌。
彩排结束,工作人员鼓掌,有人低声说:“这版太狠了,现场估计得哭一片。”
林晚舟摘下耳机,额角有细汗,胸口起伏未平。他没说话,只是走到舞台边缘,望着台下空荡荡的座位,轻声说了句:“谢谢你们还在。”
回程路上,小陈兴奋地汇报数据:“《清醒梦》上线第十天,全平台累计播放量破八千万,评论超过百万条!网易云热评第一写着:‘这首歌让我敢删掉自杀遗书草稿。’微博上有心理机构转发呼吁关注抑郁症群体,连央视新闻客户端都做了专题推送,《用音乐照亮心灵暗角》!”
林晚舟靠在车窗边,听着外面飞驰而过的风声,久久未语。
他知道,这首歌的意义早已超出了音乐本身。它成了某种信号,一种共鸣,一个让无数人敢于承认脆弱的入口。但他更清楚,这份力量并非来自他有多伟大,而是因为他曾真实地跌入深渊,并且没有假装爬出来很容易。
当晚,他独自坐在书房,打开电脑,继续整理《凌晨五点》专辑的其他曲目。他已经决定,要把这张专辑做成一张完整的自述??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为了对自己诚实一次。
他翻到一首名为《替身》的歌词,写于封杀期第三个月。那天他在酒店房间里看到电视上播出一场颁奖礼,主持人念到“最佳男歌手”时,镜头扫过替补获奖者,那人穿着和他同款的黑色西装,笑容灿烂。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可以轻易换掉一个“林晚舟”,甚至连粉丝都会慢慢适应新的声音、新的面孔。于是他写下:
>“他们找了个声音像我的人
>穿我的衣服,唱我的歌
>台下掌声雷动,没人发现
>那个站在光里的,是个影子
>而真正的我,在某个角落
>连呼吸都不敢太大声”
他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手指悬在删除键上方,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痛是真的,”他对自己说,“但藏着掖着,只会让它变成毒。”
第二天,程砚秋带来一位摄影师,是她大学时期的学姐,专攻纪实影像风格。三人开会讨论专辑视觉概念时,摄影师问:“你想让听众看到什么样的你?”
林晚舟想了想,说:“不要美化,也不要刻意惨烈。我想让他们看到‘正在进行时’的我??还没痊愈,但也没放弃。”
程砚秋补充:“封面可以用黑白,但要有光裂开的痕迹。内页放一些真实的生活片段:他弹琴的手、写满批注的歌词本、凌晨跑步的身影、甚至是他父亲墓前那张CD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