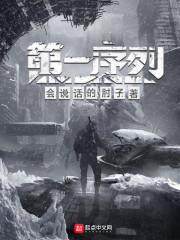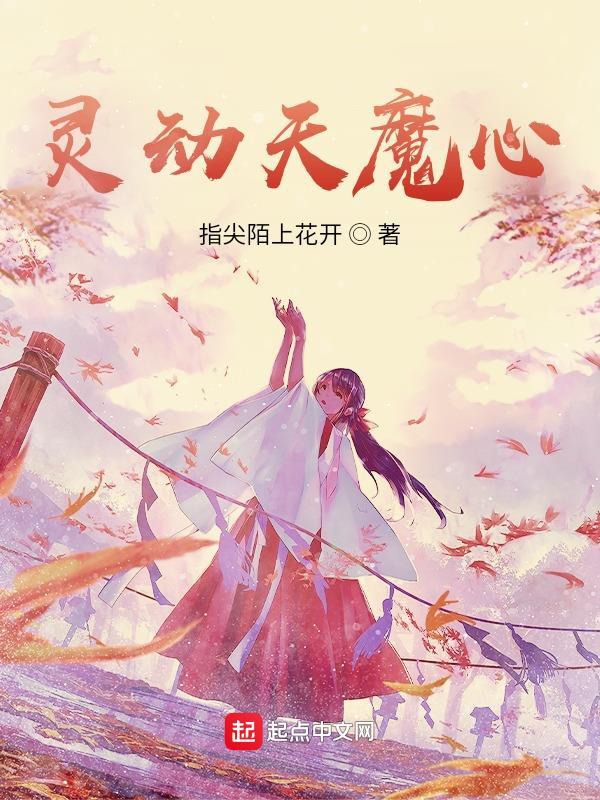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安史之乱:我手握十万兵马 > 第133章 火线立约民为城防(第1页)
第133章 火线立约民为城防(第1页)
九月初七,晨雾如纱,浸透了恒州南门校场的每一寸土地,寒意钻入骨缝。
数千名百姓被召集于此,他们中有隔离营内的幸存者,面带菜色,眼神却残存着一丝火苗;也有营外尚未染病的家属,脸上写满了忐忑与疑惧。
他们交头接耳,声音被浓雾压得低沉,汇成一片嗡嗡的背景音,像无数蜂群在巢穴边缘躁动。
赵襦阳就站在这片躁动之前,身形笔挺如枪。
他身后,一块新制的巨大木牌被两名玄甲营士卒合力竖起,遮盖的粗布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他没有多余的言语,只一个眼神示意,士卒便猛地扯下布幔。
阳光尚未穿透雾气,但木牌上用墨斗线弹出的漆黑大字,却像一道道惊雷,劈入每个人的眼底——恒州救疫十约。
人群的议论声瞬间静止,数千双眼睛死死盯着牌上的条文。
一曰“凡入营者,不得私斗,违者共逐之”;二曰“伤卒抚恤,三日公示,绝无隐匿”;三曰“粮药分配,由民推三老监之,官府不得擅动”……一条条看下来,百姓的呼吸渐渐变得粗重。
这些约定,字字句句都在约束官府,保障他们这些朝不保夕的流民。
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当他们的目光移到最后,那第十条时,整个校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官若闭城,民可破门。”
短短八个字,仿佛拥有千钧之力,压得所有人喘不过气来。
寂静过后,是轰然爆发的惊呼与哗然。
这不是约定,这是在公然煽动!
这是反书!
陈砚舟脸色煞白,他一步抢到赵襦阳身侧,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丝颤抖:“将军,三思!此约传到兵部,便是谋逆大罪,百死莫赎!”
赵襦阳没有看他,目光如炬,扫视着下方一张张或震惊、或激动、或恐惧的脸。
他看到的是濒死之人抓住救命稻草时的狂热,是绝望深渊里透出的一缕微光。
他缓缓举起手中的火漆印,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了整个校场:“不立此约,人心之信便无处可立。信若不立,恒州万民,顷刻间便会万心离散!”
话音落,他手中的赤金大印带着风声,重重地按在了木牌的右下角。
那一声沉闷的“咚”,像是惊蛰的春雷,炸响在每个人的心头。
人群中,不知是谁第一个跪了下来,紧接着,黑压压的人群如潮水般拜倒在地,额头叩击着冰冷的泥土。
他们叩拜的不是官威,而是一份敢于将身家性命与他们绑在一起的信任。
校场内的盟约刚刚订立,营外的秩序也在裴玉筝的指挥下迅速成型。
三道用石灰和草木灰划出的“灰线”将营地外围分割得井井有条。
第一重是接应区,陈砚舟的部下藏身于暗处,以特制的鸣镝为信号,指引那些从城中逃出的百姓避开官兵的巡逻路线。
第二重是检疫区,这里没有一个官兵,全由百姓自发组织的青壮设卡,他们用最朴素的方法——触摸额头,查验每一个新来者是否发热。
第三重,也是最关键的救治区,戚薇一身素衣,正将自己独创的“三洗三敷法”亲手传授给一群胆大的民妇,教她们如何用烈酒、盐水、草药灰为轻症者清创包扎,缓解医者的压力。
一个名叫阿强的壮汉,原是城中的屠户,此刻肩上扛着两袋沉甸甸的米,在三道灰线间穿行。
他的额头上绑着一条布条,上面用锅底灰写着歪歪扭扭的西个大字:“炊者不退”。
一个七八岁的孩童看得眼热,有样学样,也找了块破布系在头上,写上“药童”二字,跟在戚薇身后有模有样地递送草药。
这一幕仿佛会传染,很快,“引路”“守夜”“担水”的布条出现在越来越多人的头上,一个由民间自发形成的自治体系,竟在生死边缘奇迹般地诞生了。
营地之内,戚薇找到了疫病蔓延的真正元凶。
并非天灾,而是人祸。
那些溃兵南逃时,曾饮用过一条流经城北的河流,而那条河的上游,正有数具腐烂的战马尸体在污染着水源。
她当机立断,命人取来大量石灰铺满河岸消毒,又在两岸点燃堆积如山的艾草,用辛辣的浓烟驱逐瘴气。
对于重伤者身上不断流出的脓血,她让医童用中空的竹管小心引流,分作不同陶罐,深埋处理,避免二次感染。
夜半巡营,戚薇看到一个老妇人抱着气息奄奄的孙儿,正对着一堆篝火默默流泪,眼中满是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