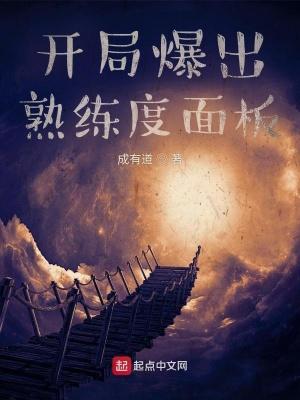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安史之乱:我手握十万兵马 > 第132章 遗孤叩首史笔如刀(第1页)
第132章 遗孤叩首史笔如刀(第1页)
天光乍破,寒气尚未从恒州城的青石板上完全褪去。
东市那面巨大的榜文前,早己是人头攒动,压抑的喘息和窃窃私语汇成一股凝重的气流。
人们踮着脚,伸长了脖子,目光如饥似渴的钉子,死死钉在那密密麻麻的墨字上,寻找着熟悉的姓名。
一个干瘦的汉子挤在最前面,浑浊的眼珠子在一行行字迹间疯狂扫视,终于,他停住了。
他的手指,枯瘦得如同鸡爪,颤抖着指向其中一个名字——“石娃子”。
名字之下,字迹清晰:“抚银十两,田五十亩,其叔石大牛代领。”
石大牛的身体剧烈地摇晃起来,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他不是不识字,他看得真真切切。
不是那句冰冷的“阵亡”,也不是敷衍的“抚恤若干”,而是有零有整的银两,是实实在在的五十亩田地。
那田,能种出粮食,能让他那刚会走路的孙儿活下去。
他想起前几日还在酒馆里咒骂赵襦阳,骂他是沽名钓誉的伪君子,骂他拿恒州百姓的性命当自己的晋身阶。
一股灼热的羞愧与巨大的感激冲垮了他所有的防线,汉子双腿一软,竟“扑通”一声朝着不远处城楼下矗立的身影跪了下去。
他用尽全身力气,将额头重重磕在冰冷的石板上,声嘶力竭地哭喊:“赵将军!我错怪您了!我石大牛不是人!您才是真心为咱们这些草芥活路的真将军啊!”
这石破天惊的一跪一喊,像一块巨石投入原本暗流涌动的湖面。
周围的嘈杂瞬间静止,无数道目光从榜文转向那个跪地的汉子,再转向城楼下的赵襦阳。
静默只持续了三息,随即,人群中响起一片压抑的抽泣声,第二个,第三个……成百上千的百姓,那些找到了亲人名字的,那些还在寻找的,那些仅仅是感同身受的,竟如潮水般齐刷刷地跪了下去。
没有谁号令,也没有谁强迫,这片由绝望和新生交织而成的叩拜,是他们能给出的最沉重的谢意。
陈砚舟站在赵襦阳身侧,看着这番景象,”
赵襦阳的目光平静地扫过一张张泪痕纵横的脸,语气淡然却掷地有声:“怕恨,就写不了真史。”
与此同时,城中一处僻静的院落里,墨香混合着松油的气味弥漫。
苏湄正仔细校对着刚刚刻好的木板,上面不是经文典籍,而是一首曲调简单的歌谣——《恒州安民歌》。
歌词质朴,讲述着一个叫戚娘的女人如何熬粥,一个叫阿强的民夫如何筑墙,一个姓赵的将军如何打开城门。
在歌谣旁边,还附印着几篇由她亲自走访记录的民间手记,《炊娘录》、《救疫记》,字字句句皆是普通人的血泪与挣扎。
她将一叠刚印好的纸张交给整装待发的商旅:“劳烦各位,将这些带往各州,无需售卖,赠予说书人、歌姬,或是贴在人多的茶馆驿站即可。”
做完这一切,她来到赵襦阳面前,将一份样稿递给他。
“百姓大多不识字,朝廷的邸报他们也看不懂。但他们会唱歌,会听故事。”她的声音清澈而坚定,“歌里有您,有戚娘,有阿强,有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史官的笔可以删去您的功绩,却删不了这万口传唱的歌谣。”
赵襦阳接过那尚带着油墨温度的纸,目光在那些朴素的文字上停留了很久,最终,他抬起头,深深地凝视着眼前的女子,良久,才发出一声复杂的叹息:“你才是真正的史官。”
话音未落,城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
午时,兵部的问罪使者己至城外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