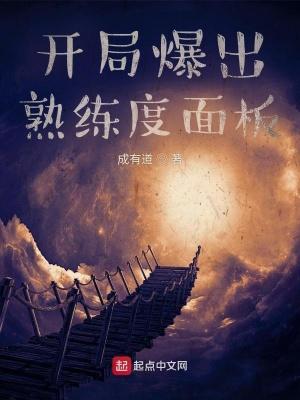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安史之乱:我手握十万兵马 > 第132章 遗孤叩首史笔如刀(第2页)
第132章 遗孤叩首史笔如刀(第2页)
赵襦阳没有披甲,没有列兵,身后只跟着手捧抚恤名册与《流民安置策》的陈砚舟,亲自出迎。
使者一行人马高头,甲胄鲜明,为首之人面色倨傲,勒马停住,看也不看赵襦阳,便从怀中掏出文书,厉声宣读:“恒州守将赵襦阳,罔顾军令,擅开城门,收纳数千溃兵,形同谋反!着即刻……”
“使者大人。”赵襦阳打断了他,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遍在场每个人的耳朵。
他示意陈砚舟上前,当众展开那厚厚的名册。
“此册,共录三千六百二十一人。每一个名字后面,都详录其籍贯、所属部队、伤情、以及抚恤去向。您要问罪,不如先从这名册上,随意报出一人之名,告诉我,他该不该死,他的家人该不该活。”
使者被这一下噎得满脸通红,他哪里知道什么名字,他只知道自己奉的命令。
他身后跟随而来的百姓却炸开了锅,不知是谁第一个高喊:“他们是我兄弟!要问罪,连我一起问!”
“我丈夫就在里面!他为国杀敌,断了一条腿,难道连回家的门都不能进吗?”
“将军救了我们全家!要定将军的罪,先从我等的尸体上踏过去!”
数千百姓自发围拢过来,群情激愤,声浪滔天:“我等愿与将军共担此罪!”
使者的脸色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他带来的几十名护卫在这人山人海的怒吼中,渺小得如同孤舟。
夜色深沉,白日的喧嚣归于平静,但暗流却愈发汹涌。
一封加急密信被送到赵襦阳案头,火漆上是杜鸿渐的私人印记。
烛火下,信纸上的字迹显得格外凝重:“灵武己尽闻恒州开城之事。太子殿下未有申饬,似为默许。然,宦官鱼朝恩正借此大做文章,欲以此为由,削你兵权,夺你恒州。万望谨慎。”
赵襦阳燃尽信纸,青烟袅袅。
他提起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一行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然舟若无舵,终为浪吞。
他唤来心腹薛七郎,将那份《流民安置策》递过去,沉声吩咐:“连夜抄录七份,用最快的马,一份送往太原李光弼将军处,一份送给朔方郭子仪将军旧部,其余五份,分送河北七州仍在坚守的刺史。告诉他们,恒州有地安置流民,亦有策安抚人心。”
子时,万籁俱寂。
赵襦阳独自一人登上鼓楼,冰冷的夜风吹动他的衣袍。
他手中着一片干瘪的麦穗,那麦穗的源头,与他送往灵武太子案头的那一串,来自同一片田地。
他望着沉沉夜幕下的万家灯火,低声自语:“你们在史书上写我是拥兵自重的叛将,我便做那护佑万民的逆臣;你们在朝堂上删我功名,我便让这功名,在百姓的口中代代相传。”
话音刚落,一阵微弱而杂乱的鼓声,隐隐约约从城外极远的地方传来,仿佛是黑夜疲惫的心跳。
陈砚舟匆匆登上鼓楼,神色凝重地来报:“将军,城外又有溃兵赶来,看火把绵延,不下千人,其中……似乎还有大量的妇孺。”
赵襦阳猛地站起身,将那片麦穗收入怀中,毫不犹豫地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下鼓楼,口中发出清晰而决绝的命令:“传令下去,开城门!城墙上,多点灯笼——”
他顿了顿,声音在夜风中传出很远,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力量。
“要足够亮,照亮他们每一个人回家的路。”
风,在这一刻骤然变大,卷起他的衣角,也卷起了城外那愈发清晰的鼓声。
灯火与鼓声在无边的黑夜中交织,仿佛正用最原始的方式,在这乱世的画布上,刻下一道永不磨灭的史痕。
而城中刚刚安睡的人们尚不知道,当第一缕晨曦刺破这漫漫长夜时,一场决定他们所有人命运的集会,己在酝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