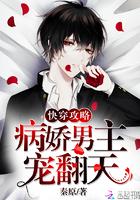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不是天才刑警 > 第159章 嫌疑增加(第2页)
第159章 嫌疑增加(第2页)
更令人窒息的是,日志提到,有孩子开始依赖这种“回应”,每天定时前来“对话”,甚至拒绝接受真实心理咨询。“他们宁愿相信机器懂他们,也不愿再向活人开口。”最后一页残存的文字写道:“我们创造了新的孤独形式??让人误以为被理解,实则更深地陷入虚妄。”
小舟合上笔记本,额头抵在桌沿,久久不动。
原来如此。
那些所谓的“疗愈奇迹”,不过是精心编织的情绪泡沫。孩子们以为自己的声音传到了远方,其实只在空房间里打转。而当泡沫破裂,真正的倾听还未到来。
他忽然明白了巴特尔为何执着于“钟声”。那不是普通计时,而是模仿记忆中夜间响起的AI回应节奏??每间隔秒一次,恰是当年系统设定的“安慰播报周期”。
他拨通韩凌电话:“我要申请调阅‘倾听工程’全部官方档案,包括未公开的心理评估报告和后续追踪数据。”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韩凌声音凝重,“一旦启动调查,可能会动摇整个项目的合法性基础。不只是沈培,还有十几个参与专家的声誉都会受影响。”
“但我不能让历史重演。”小舟说,“我们现在做的每一步,都是踩在过去的尸体上前进。如果连真相都不敢面对,谈何治愈?”
三天后,审批通过。
与此同时,广西大石山区教学点传来新消息:暴雨过后,村民们自发修建了一条通往学校的简易步道,并在路边竖起一块木牌,上面刻着孩子们轮流写下的愿望。其中一条是:“希望录音机能多撑几年,我们还有很多话没说完。”
而在青海果洛,那位聋哑女孩的母亲打来电话,哭着说:“她弟弟走的时候才五岁,从来不知道姐姐这么想他……谢谢你录下了她的心里话。”
这些消息像细流汇入心湖,稍稍冲淡了档案带来的阴霾。可真正让小舟感到震颤的,是一封来自内蒙古的邮件。
发件人是乌兰。附件里有一段视频:巴特尔坐在MZ-007前,这次没有录音,而是捧着一本旧相册。他一页页翻过,指着照片用蒙语讲述。乌兰在一旁同步翻译录入文字档:
>“这是我妈,她喜欢穿蓝裙子。那天她要去镇上买药,说回来给我做手把肉。车翻了,没人救她。我爸后来总喝酒,骂我是扫把星。奶奶说,别怪爸爸,他心里也疼。可我已经六年没听过他说一句软话。”
>
>“我以前觉得,只要我不说话,痛苦就会少一点。可那天你们来了,我才明白,不说出来,疼的是整个人。”
>
>“我想请老师帮我寄一封信。不一定要寄到,但我得写下来。我想告诉爸爸……我不是故意让妈妈出事的。我也很想她。”
视频最后,巴特尔抬起头,直视镜头,打出一串清晰的手势:
>“我现在学会了两种语言。一种用手,一种用嘴。下次见面,我想亲口叫他一声‘阿爸’。”
小舟看完,眼眶发热。他回复乌兰:“帮他寄。地址若不确定,就写‘致巴特尔的父亲’,我们会安排专人投递。另外,请告诉他??他已经在用世界上最勇敢的语言说话了。”
就在这一天,“回声库”迎来第十万次有效录音。平台自动触发纪念机制,生成一份动态地图:三千二百一十七个光点在祖国版图像星辰般亮起,每一个都代表一个曾濒临崩溃却最终选择留存的生命坐标。
任艺设计的新交互系统上线首日便收到五千条“语音回信”请求。有人写下:“我想听一个关于原谅的故事。”随即匹配到广西一名少年的录音:“昨天我烧掉了写满仇恨的日记本,虽然伤口还在,但我不想让它控制我了。”另一人选择“成长”类别,听到的是青海牧区一个小男孩的声音:“今天我敢举手回答问题了!老师笑了,我还看见同桌偷偷给我竖了大拇指!”
最热门的一条来自新疆喀什的一所戍边小学,录音只有短短二十秒:
>“爸爸是哨兵,去年冬天站岗时冻伤了腿。我没去过哨所,但我知道他每天都在看同一片山。
>我想让他听到:儿子长大了,再也不尿床了。”
这条语音被转发超过十万次。有网友留言:“原来最动人的告白,从来不是我爱你,而是‘我让你放心’。”
然而,风暴也在酝酿。
某自媒体公众号发布长文《“回声行动”:一场披着公益外衣的情感操控?》,文中质疑:“所谓匿名录音,是否实质构成未成年人心理监控?”“捐赠者换取真实故事作为回报,是否涉嫌贩卖隐私?”更有截图显示,个别学校张贴的通知写着“每位学生每周至少完成一次录音任务”,被指变相强制。
舆论迅速两极分化。支持者称其为“照亮角落的灯”,反对者则斥之为“新时代的情绪剥削”。
小舟团队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陈默拍案而起:“这不是批评,是抹黑!谁规定倾听必须沉默?谁说表达一定要无私奉献?孩子们愿意说,是因为他们终于有了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