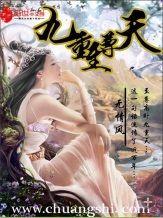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不是天才刑警 > 第156章 发现尸体恢复更新(第2页)
第156章 发现尸体恢复更新(第2页)
“我去发言。”小舟抬起头,眼神清澈而坚定,“你是创始人,但你是大人。而我是那个真正坐在教室里,听着别人说出‘我害怕’‘我讨厌我爸’‘我觉得我不配活着’的人。我知道这些话有多重,也知道当有人安静听完时,那种轻了多少的感觉。”
任艺看着他,忽然笑了:“你知道吗?你现在的样子,特别像韩凌七年前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样子。”
韩凌沉默片刻,伸手揉了揉小舟的头发。“那就一起准备吧。不过你要记住,台上一分钟,台下三个月。我们需要案例、数据、视频素材,还要预判所有可能的攻击点。”
接下来的日子,像一场无声的战役。
白天,小舟带着志愿者整理学生录音精选集,剔除敏感信息后转化为匿名文本;晚上,他和韩凌反复修改演讲稿,把抽象理念转化成具体场景。比如:
>“当一个孩子说‘我妈骂我是废物’,我们不该回答‘别这么说自己’,而是问:‘那你听到这句话时,心里是什么感觉?’
>不是否定痛苦,而是承认它的存在。”
他们还制作了一段五分钟纪录片,记录一名自闭倾向男生如何通过“布老虎倾听法”第一次主动发言;另一名曾休学半年的女孩,在匿名录音中倾诉抑郁后,收到了来自陌生城市的纸鹤明信片,上面写着:“我也曾躲在被子里哭,但现在我在晒太阳,你也试试看?”
与此同时,陈默也没闲着。他联合几位营养学家和心理学家,正式推出“味觉记忆库”的升级版??**情感食疗计划**。针对孤独症儿童、阿尔茨海默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人群,开发带有语音引导的定制菜谱。
>“比如为失语老人设计一道‘童年豆腐羹’,烹饪过程中会播放上世纪八十年代街头叫卖声、收音机广播片段,唤醒深层记忆。”
>“又或者为失去孩子的母亲准备‘宝宝辅食回溯套餐’,每一步都有温柔女声解说:‘你现在做的,是他曾经最爱吃的南瓜泥。’”
项目上线当天,一位七十多岁的父亲留言:“我老伴走了三年,从来不提儿子的事。昨晚她跟着语音做了韭菜炒鸡蛋,做到一半突然哭了。那是她第一次说起车祸那天,儿子最后说的话是:‘妈,我想吃你炒的蛋。’”
这条评论被韩凌放进大会材料附录,标题为:**食物不是终点,是通往记忆的桥**。
出发前夜,小舟独自爬上福利院屋顶。雪已停,星空清澈如洗。他打开录音笔,对着夜空说话:
>“妈妈,今天我好像要做一件大事。
>韩叔叔说,很多人会听我说话,也许还能改变一些东西。
>我有点怕,怕说错话,怕不够勇敢。
>但我想起你说过,真正的勇气不是不害怕,而是背着害怕往前走。
>所以我会努力的。
>如果你能听见,请给我一点风,告诉我你在。”
话音落下,一阵微风拂过耳畔,吹动了屋檐下的铃铛。叮铃,叮铃,像是回应。
第二天清晨,三人踏上北行列车。窗外风景飞速后退,城市、田野、山峦接连掠过。小舟靠在窗边,手里攥着那张写满批注的讲稿。他在页脚加了一句新守则:
>**4。当世界要求你坚强时,允许自己软弱一次,只要你还愿意开口。**
北京会场设在国家教育研究院礼堂。阶梯式座位环形排列,灯光柔和,气氛庄重。台下坐着各省教育厅代表、心理专家、媒体记者,以及几位曾参与早期试点的校长。
沈培主持开场,目光扫过全场,最终落在小舟身上。
“今天我们请来一位特殊发言人。”他说,“他不是教授,不是官员,甚至还没成年。但他亲身经历了‘回声计划’带来的转变。让我们听听,来自真实课堂的声音。”
掌声响起。小舟站起身,走向讲台。脚步有些迟疑,但每一步都稳稳落下。
他没有用PPT,也没有念稿。只是掏出那台老旧的录音机,放在话筒前。
“我想先放一段声音。”他说,声音不大,却清晰传遍全场。
喇叭里传出稚嫩的童音:
>“我希望妈妈能看见我跳舞。”
>“我觉得韩叔叔像个树洞,说什么都不会笑话你。”
>“我也要成为别人的灯。”
接着,是一阵电流杂音,然后恢复平静。
“这是三年前,我们挂在槐树上的第一台录音机录下的。”小舟说,“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项目能不能活下去,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听。但我们还是录下了这些话,因为我们相信??**有些声音,哪怕只被一个人听见,也值得存在**。”
他顿了顿,看向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