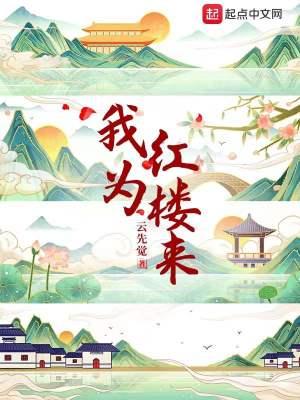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不是天才刑警 > 第155章 搜索李德昌(第3页)
第155章 搜索李德昌(第3页)
>“当年我们失败,不是因为方法错,而是时代还没准备好倾听。现在,它准备好了吗?”
韩凌把照片贴在办公室墙上。旁边是他新写的一页笔记:
>“改变从来不是轰然降临的。它始于某个孩子鼓起勇气说出‘我害怕’,始于某个父亲听见儿子说‘我原谅你’,始于某个陌生人愿意为一句‘我还在这里’而停留。”
八月初,“灯芯社”发起“城市回音墙”行动。他们在城市各个角落设置小型录音亭,外观像旧式电话亭,内部配有按钮和扬声器。路人可以进去录一段话,也可以随机听到别人留下的一句话。
第一周,有人录下求婚告白,有人倾诉职场委屈,也有人单纯说:“今天太阳真好,我想分享给你。”
但也出现了恶意内容。一条辱骂女性的录音被投放出来,引发公众愤怒。有人指责“回音墙”缺乏监管,是“垃圾情绪的垃圾桶”。
韩凌连夜召开会议,决定引入双轨机制:公开播放的内容需经过AI初筛与人工复核,而原始录音则加密保存,仅用于后续心理援助对接。
他在发布会上说:“我们不能因恐惧而封锁声音。但我们必须学会,在自由与责任之间架桥。”
令人意外的是,那条辱骂录音的发布者主动联系了平台。他是一个失业青年,说自己那天喝醉了,把生活中的挫败感发泄到了陌生人身上。在听了其他人的善意留言后,他哭了:“我以为这个世界只剩对抗,没想到还有人在认真听。”
他自愿加入“灯芯社”做义工,每周去养老院陪老人聊天。他说:“以前我觉得说话是为了赢,现在才知道,是为了连接。”
秋意渐起时,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小舟在树下埋了一个铁盒,里面装着他这一年所有的录音带、日记和同学们写给他的卡片。他还放进了一张画,是他梦见妈妈的样子??她站在一片开满槐花的山坡上,冲他挥手。
“等树长高了,我就挖出来看。”他说。
韩凌蹲在一旁,帮他把土拍实。小舟忽然问:“你说,妈妈真的能听见我说话吗?”
韩凌望着树冠,风吹过,叶子簌簌作响。“我不知道科学怎么解释。”他说,“但我知道,当你相信她能听见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人在长大。”
那天晚上,韩凌独自回到疗养院旧址。月光洒在空荡的大厅里,他打开随身携带的录音笔,按下录制键:
>“林昭教授,我是韩凌。您当年没能完成的事,现在有人接着做了。
>您说‘治愈始于尊重,而非纠正’,我现在懂了。
>我们不再急于解决问题,而是先蹲下来,看看那个哭泣的人眼里有什么。
>这世界依旧不完美,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成为一盏微弱的灯。
>而我,也还在路上。”
他关掉录音,走出门。夜风拂面,远处传来孩童嬉笑的声音。他知道,那是福利院的孩子们在玩捉迷藏。
他抬头望向星空,轻声说:“听见了就好。”
几天后,市教育局正式批复,“回声校园计划”将在全市推广。文件末尾特别注明:“该项目不仅培养表达能力,更重建了人与人之间的倾听伦理。”
同时,“回声”平台注册用户突破百万。后台数据显示,超过六成用户连续使用超过六个月,平均每人留下十八段录音。最常出现的开头是:“其实我一直想说……”
韩凌在年度报告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们曾以为,拯救是从深渊拉人上来。后来才发现,真正的拯救,是让那个人自己愿意伸手。
>而我们的角色,不过是蹲在井边,轻轻说一句:‘我听见了。你不用一个人扛。’”
冬雪初降的那个清晨,小舟带着全班同学来到槐树下。他们每人带来一颗种子,种在树周围,围成一个圆圈。
“这是我们的‘声音森林’。”小舟说,“以后每一棵树,都会记住一个故事。”
韩凌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孩子们冻得通红的脸颊和明亮的眼睛。他摸了摸口袋里的录音笔,里面存着最新一条用户留言:
>“我抑郁症十年,从未跟人提起。昨晚我录了音,说:‘我好累,但我不想死了。’
>今早醒来,有十七个人听了,其中一个说:‘谢谢你坚持到现在,我陪你一起。’
>我哭了好久。原来我不是废物,我只是太久没人肯听我说话。”
他走出院子,踏上积雪的小路。天边微光渐亮,城市慢慢苏醒。
他知道,这场关于倾听的革命,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