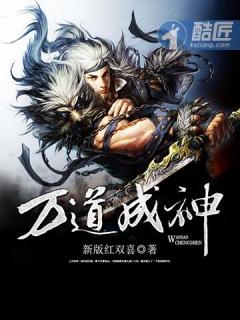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我不是天才刑警 > 第155章 搜索李德昌(第1页)
第155章 搜索李德昌(第1页)
二十分钟后。
市局。
专案指挥中心接到了负责监控、保护李德昌警员的电话。
四名支队民警在十分钟前赶到了建筑工地,但一直没有见到李德昌,此刻距离双方原本约定的见面时间,已经超过了二十分。。。
夜雨来得突然。六月的风裹着湿气撞进窗缝,韩凌没关灯就走了,桌上还摊着昨天未整理完的用户反馈表。雨水顺着屋檐滴在槐树新叶上,发出细碎的响声,像谁在低语。
小舟是被雷声惊醒的。他坐起身,布老虎滑落在床边,窗外一道闪电劈过,照亮了挂在树枝上的录音机。他忽然想起昨晚忘记换带子了??那盘磁带已经录满了孩子们的声音,再不停止,后面的会覆盖前面的。
他披上外套跑出去时,雨正越下越大。泥水溅上裤腿,凉意顺着脚踝爬上来。录音机被塑料布勉强遮住,但接口处已渗进水珠。他慌忙按下倒带键,手指发抖,生怕那些声音就这样消失了。
“别坏……别坏……”他喃喃着,耳朵贴在喇叭边听。电流杂音里,依稀还能辨出几个孩子的声音:“今天我背下了整首《静夜思》。”“我希望妈妈能看见我跳舞。”“我觉得韩叔叔像个树洞,说什么都不会笑话你。”
然后,是那一句??
>“我也要成为别人的灯。”
小舟松了口气,可就在这时,录音机“咔”地一声停了。电源接触不良,彻底断了电。
他蹲在树下,抱着机器不动。雨水顺着头发流进眼睛,涩涩地疼。他知道这台老式录音机经不起太多折腾,张建国说过,这种型号早就停产了,零件都靠拼凑。要是坏了,可能再也修不好。
不知过了多久,一只手轻轻搭在他肩上。韩凌穿着雨衣站在背后,手里提着工具箱。
“我听见你在喊。”他说,“走吧,带回去试试。”
两人挤在值班室的小桌前,拆开外壳,用吹风机小心烘干电路板。韩凌动作很轻,像是在处理一封年代久远的信。小舟盯着他的手,忽然问:“你会修所有东西吗?”
韩凌笑了笑:“不会。但我愿意试。”
半小时后,录音机重新响起。第一段声音是福利院李奶奶清早念的菜谱:“今天炖排骨,放两片姜,一点料酒……”接着是孩子们轮流说话的画面,最后,又是那句??
>“我也要成为别人的灯。”
小舟抬头看着韩凌:“这句话是你写的,对不对?”
韩凌没否认。他把录音机放回桌上,低声说:“七年前,我还在警队的时候,接到一个跳楼案。现场是个二十岁的女孩,她留下一段录音,只有一句话:‘有没有人,愿意当我的灯?’
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一个人非得等到快熄灭了才敢开口。后来我才明白,不是她们不想说,而是这个世界太吵,把她们的声音盖住了。”
小舟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站起来,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纸。“我也写了个守则。”他说,“我想加到你的本子里。”
韩凌接过一看,上面用铅笔写着三条规则:
1。每天至少听一个人说完一句话,不打断。
2。如果有人哭了,不说“别哭”,而是陪着他。
3。记住别人的名字,哪怕他觉得自己不重要。
“这是我在‘沉默十分钟’课上学来的。”小舟说,“老师讲完‘回声’的故事,让我们写自己想守护的东西。我就写了这些。”
韩凌看着那几行字,喉头微动。他打开笔记本,在《共感伦理守则》下方,郑重添上第四条补充条款:
>“倾听者亦可立法。每一份真心,都是光的刻度。”
第二天清晨,阳光穿过云层洒在湿漉漉的院子里。槐树叶子闪着光,像挂满小小的镜子。小舟把录音机重新挂在树杈上,这次用了防水袋和铁丝牢牢固定。
任艺一早打来电话:“论坛上的录音片段全删了,源头查到了,是个辍学少年,自称‘只是想找点存在感’。他母亲联系了我们,说孩子最近三个月没说过超过十句话……我们安排了心理介入。”
“让他听听‘灯芯社’的录音吧。”韩凌说,“有时候,最深的孤独,不是没人陪,而是连表达痛苦的方式都不知道。”
挂掉电话,他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附件是一段音频,标题叫《第一次》。播放后,是一个沙哑的男声:
>“这是我第一次给别人录音。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我一直恨我爸,因为他在我妈走后娶了别人。我搬出去五年,一次都没回去过。
>昨天我路过小时候住的老楼,看见他在阳台上浇花,背都驼了。我站在楼下看了很久,最后掏出手机点了这个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