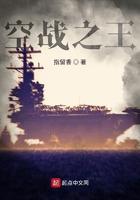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状元郎 > 第三六八章 文魁的威力(第2页)
第三六八章 文魁的威力(第2页)
刘丙猛地站起:“若真如此,岂非是我等险些冤枉忠良?此语若属实,便是第一手史料,价值连城!更何况,考生竟能指出内阁藏书编号,足见其曾入阁查阅典籍,学识渊博至此,何止举人?进士亦不过尔尔!”
张彦凝视手中试卷,缓缓道:“此人头场八股,虽不如前卷那般惊才绝艳,然结构谨严,用典精准,尤以‘礼因时而制,义随时而变’为核心命题,层层推进,逻辑严密。二场对策论‘边防屯田利弊’,提出‘以耕养战,以商助军’之策,极具操作性。三场判语更是老辣,一道《断豪强夺产案》,引《大明律》与《春秋》经义互证,断案如神,毫无滞碍。”
他顿了顿,转向徵德先生:“先生为何起初未能识珠?”
徵德先生羞愧低头:“一则因其破题用语大胆,不合常规;二则……老朽心中先存偏见,以为寒门学子断无可能知晓内阁秘藏。是以轻率下笔,几致埋没国士。如今回想,汗颜无地。”
张彦摇头道:“不能全怪先生。科场取士,本就易为成见所蔽。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此人既能写出如此文章,自有冥冥之力助其昭雪。如今既已发现,便不可再误。”
他提笔在朱卷上重重批下四个大字:“特荐解元”。
满堂寂静。
良久,刘丙低声道:“可是……已有前卷堪称完美,若再立一解元,岂非悖理?”
张彦目光坚定:“非常之才,当行非常之举。我意已决??本科双解元并列!”
“什么?!”众人齐惊。
“双解元”乃百年未闻之事。自开科以来,每省乡试仅录一名解元,以示独尊。纵有并列之议,亦从未实行。
张彦却不为所动:“何谓解元?解者,解惑也;元者,首善也。凡能解国家之惑、为士林之首者,皆可称解元。今有二人,一以才胜,一以识胜;一通天人之际,一达古今之变。二者皆旷世奇才,若强分高下,反失公允。不如并列榜首,彰我七川文运昌隆!”
刘丙沉吟许久,终于展颜笑道:“好!就让这届乡试,成为载入史册的一科!双星耀蜀,光照千秋!”
吴坤亦抚掌而笑:“既然两位主考同心,本官也不再多言。只是此事须报礼部备案,恐怕会引起朝中议论。”
张彦凛然道:“议论由他去。我只问一句:可曾辜负国家?可曾辜负考生?若皆无愧,何惧人言?”
话音落下,窗外忽有疾风掠过,吹动帘幕翻飞,似天地为之动容。
就在这时,一名小吏匆匆奔入,跪禀道:“启禀主考大人,外头有个少年书生跪在贡院门前,自称是那份‘礼非死物’试卷的作者,恳请面见主考,澄清误会!他说……若因自己引用冷僻文献而被黜落,宁愿当场自废功名,终身不入科场!”
张彦霍然起身:“快请进来!”
不多时,只见一个青衫褴褛、面容清瘦的少年被引入堂中。他双膝跪地,额头触地,声音哽咽:“学生杜陵,叩见大宗师。学生无意冒犯,只为阐明圣训真义。若有半句虚言,愿受天雷殛顶!”
张彦亲自扶起,细细打量,只见其眉宇间英气内敛,眼神清澈如泉,毫无骄矜之色。
“你可知,你这一句话,几乎让你名落孙山?”
少年垂首:“学生知道。但若因畏惧而不言真相,才是真正的辱没圣贤。学生宁可不中,也不能让真理沉默。”
张彦仰天大笑:“好!好一个‘宁可不中,也不能让真理沉默’!这才是我辈读书人的脊梁!”
他转身对众官朗声道:“诸君请看,此子不但学问过人,品格尤高。如此人物,岂能屈居人下?传令下去??本科解元,杜陵、李昭(前卷作者)并列!张榜明示,天下共鉴!”
当日黄昏,成都贡院外锣鼓喧天,红榜高悬。
百姓争相传诵:“七川出双杰,一卷惊风雨,一语动乾坤!”
而在衡鉴堂深处,张彦独自伫立窗前,望着渐沉的夕阳,低声吟道:
“天以无穷覆,地以厚重载。圣人之道,不在庙堂之高,而在匹夫之志。今日所取者,非止二人,乃万千寒门希望之所寄也。”
风起卷帘,案上两份朱卷静静并列,墨香氤氲,仿佛预示着一段新的传奇,正从这片土地上悄然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