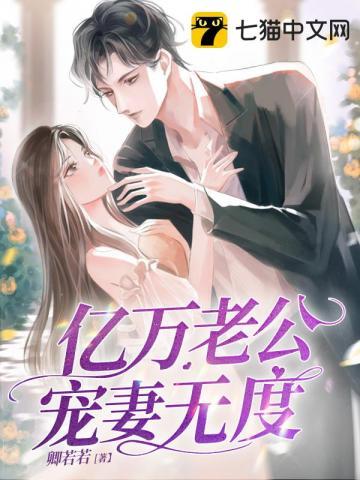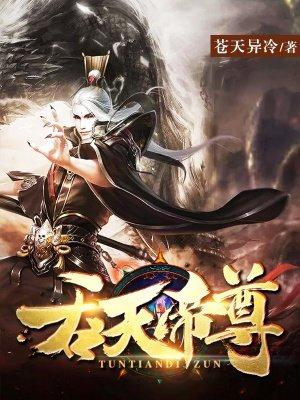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状元郎 > 第三六三章 赢了(第3页)
第三六三章 赢了(第3页)
奏疏尚未呈递,宫中已有耳目得知内容。杨廷和冷笑:“一个被削了解元的乡间腐儒,也敢议政?”遂下令通政司拒收。
可三天后,这份条陈竟出现在皇帝案头。
原来,太子朱厚?私自截留,并力劝叔父一阅。正德帝本无意细看,却被其中一段打动:
“臣尝见一老妪,因其子战死边关,领抚恤银时因不识字,被吏员欺吞大半。归家后痛哭绝食,三日而亡。陛下试问,此非制度之罪乎?若人人识字,则奸吏无所遁形;若层层设监,则贪蠹不得滋生……”
皇帝沉默良久,提笔批道:
“此疏颇有见识,着内阁议复。”
杨廷和勃然大怒,立即召集心腹谋划反制。他深知,若让苏录在京立足,必将动摇其执政根基。于是密令锦衣卫调查其过往言行,务求找出“悖逆证据”。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边关急报传来:
安南莫登庸叛乱,侵扰广西,杀死守将二人,边民死者数千。朝廷震怒,急召廷议。
兵部主张派大军征讨,耗费巨万。户部叫苦连天,称国库空虚,难以支撑。正当群臣束手之际,苏录通过聂豹递上第二道奏疏:《平蛮三策》。
其策曰:
一、不动大军,选精干文官携《识字课本》深入峒寨,教化夷童,使其渐慕华风;
二、扶持当地归顺土酋,赐匾授印,分化叛党;
三、开通互市,以盐铁换粮草,使边民生计有所依,则叛乱自息。
“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安南之乱,实因贫苦无知所致。与其劳师远征,不如以文化之。”
此策一出,满朝哗然。多数大臣讥为“书生空谈”。可兵部侍郎王宪却极力赞成:“近年征苗耗费百万,愈平愈乱。或许,真该换个法子试试。”
最终,皇帝采纳折中方案:暂不发兵,先遣两名文官试行招抚。其中一人,便是苏录。
出发前夜,聂豹警告他:“这是把你推出去挡箭。若成功,功劳归朝廷;若失败,你就是替罪羊。”
苏录笑了:“我早不是为了功劳而来。”
两个月后,他抵达广西太平府。面对瘴疠横行、语言不通的困境,他并未急于进山,而是先在当地建起十所“蒙学堂”,招募通晓壮语的译者,将《识字课本》翻译成土话版本,逐字教授。
半年之内,数百峒寨孩童学会书写姓名,能读简易告示。更有部落首领主动派人前来询问:“你们教孩子认字,不要钱?”
苏录答:“我们要的不是钱,是和平。”
一年后,莫登庸内部生变,其弟受朝廷册封,率部归降。边境战火渐熄。
捷报传回京城,朝野震惊。那些曾嘲笑苏录“以书卷退敌”的大臣,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被贬黜的年轻人。
而此时的苏录,正坐在一座山寨的火塘边,教一个五岁女童写下自己的名字。炭笔在粗纸上划出歪斜的一横一竖,孩子咯咯笑着,把纸举给母亲看。
火光映照着他清瘦的脸庞,额角已有风霜刻痕。
他知道,这场变革不会止于广西,也不会止于识字。
他要让整个大明知道??
真正的权力,不在紫禁城的金銮殿上,而在千万双终于能够阅读的眼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