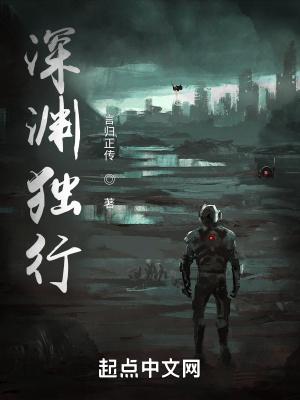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状元郎 > 第三六三章 赢了(第1页)
第三六三章 赢了(第1页)
成都城北三十里,藏一汪灵秀桂湖,形似琵琶,湖水如碧。因沿岸广植桂树,金秋时节,香飘数里而得名。
湖畔筑有一座私家园林,唤作桂园,乃杨氏一族的别业,位于杨氏祖宅之西。
园内亭台楼阁沿湖而建,。。。
风雨未歇,晨雾如纱笼着贡院照壁。苏录立于高台之上,手中锦旗猎猎作响,红底金字“四川乡试解元”在微光中灼目刺眼。他未曾低头看那旗帜一眼,目光越过攒动的人头,投向城南方向??那里是巡抚衙门旧址,如今空荡如墓。
人群喧沸,有书生高呼:“弘之先生救世文章,今日终得正名!”也有老儒拄杖怒斥:“狂生乱政,祖制岂容轻议!”一纸揭帖被人当众焚烧,火光映出围观者脸上扭曲的明暗。一名卖字摊前的老叟默默收起自己抄录的《四书义》稿本,塞进竹箧深处,仿佛藏起一段禁忌历史。
苏录缓缓走下台阶时,肩头忽被按住。回头,是萧提学湿漉漉的手掌。老人鬓发斑白,眼眶泛红,声音压得极低:“他们要压你,可你也逼得太狠。”
“学生知错。”苏录轻声道,“但若不如此,谁肯听寒门一言?”
萧提学长叹,从怀中取出一封密函:“这是许尚书亲笔,昨夜飞骑送达。他说……朝廷已有风声,杨廷和欲借此次‘谤议案’清洗川中文官系统,连刘中都可能遭贬。”
苏录拆信细读,指尖微颤。信末一句:“**君为星火,我辈护之以风,勿自熄灭**。”
他将信焚于灯上,灰烬飘落泥水之中。
当日午后,成都府衙设宴庆贺新科举人。苏录推辞再三,终因礼不可废而赴席。酒过三巡,布政使刘中举杯致辞,语带哽咽:“今岁蜀中得此俊才,实乃苍生之幸!”话音未落,堂外骤然传来马蹄急响。
一名驿卒浑身泥浆冲入厅内,跪地呈报:“京师急讯!吏部传令:新科解元苏录,即日起暂停殿试资格,待查清试卷是否‘非议朝政’后再行定夺!”
满座哗然。
杨慎端坐席间,不动声色,只轻轻抿了一口酒。他身旁几位同年低声议论:“果然是太过锋芒。”“怕是要步李卓吾后尘了。”
唯有苏录神色不变,起身拱手道:“既奉旨意,学生自当静候审查。不过,请转告中枢诸公??我所写每字皆出肺腑,愿对天子当面陈词,无悔无惧。”
刘中脸色铁青,连夜召集幕僚商议对策。次日清晨,八百里加急奏折已送往通政司,附录三场答卷全文,并请都察院御史联名担保“并无悖逆之语”。同时,萧提学发动川南书院联盟,三百余名教谕联署上书,称“苏录之文,理胜于辞,忧国深矣”,恳请宽宥直言之士。
然而七日后,京中回复冰冷无情:
“苏录策论中‘权不在人而在制’一句,涉嫌动摇君臣纲纪;提及阳明讲学事,逾越士子本分。着令暂黜功名,待详勘定罪。”
消息传出,全川震动。
泸州、叙州、嘉定等地书院学子纷纷罢课,集会声援。有青年书生徒步百里至成都,在贡院门前长跪不起,手持白幡书曰:“还我真才!”更有甚者,夜闯按察使司衙门,留下血书:“杀一贤者,失万民心!”
而就在这片沸腾之中,一道身影悄然离开成都,北上入京。
聂豹。
这位阳明门下最锐利的言官,在通政司递上第三道奏疏。文中直指杨廷和:“昔汉武抑百家而尊儒术,然犹容汲黯抗言;唐太宗恶魏徵屡谏,终谓之‘镜鉴’。今首辅以一己好恶,禁天下敢言之声,岂非重蹈吕诲攻王安石之覆辙?且苏录所倡,非毁祖宗,乃复洪武初制??彼时本无巡抚专权,三司分治,正合太祖遗训!”
此疏一出,朝野侧目。
内阁震怒,杨廷和亲自批驳:“迂腐书生,不知大体!”随即下令锦衣卫查抄聂豹宅邸,搜得其与苏录通信数封,皆论教育改革、地方自治之事。虽无谋逆之词,却被定性为“结党妄议国政”。
眼看局势恶化,一道意想不到的声音响起。
太子朱厚???当今圣上之侄,兴王世子??竟在东宫讲筵中公开称赞苏录文章:“此人虽年轻,却看得深远。我大明若再不改弊政,恐难撑百年。”
此言经讲官传入内廷,皇帝为之动容。加之户部尚书梁储、兵部侍郎王守仁旧部暗中运作,终于迫使内阁退让一步:
“准苏录保留举人身份,解元称号撤销,殿试资格延至三年后,视其行为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