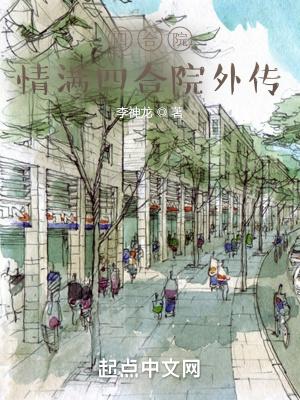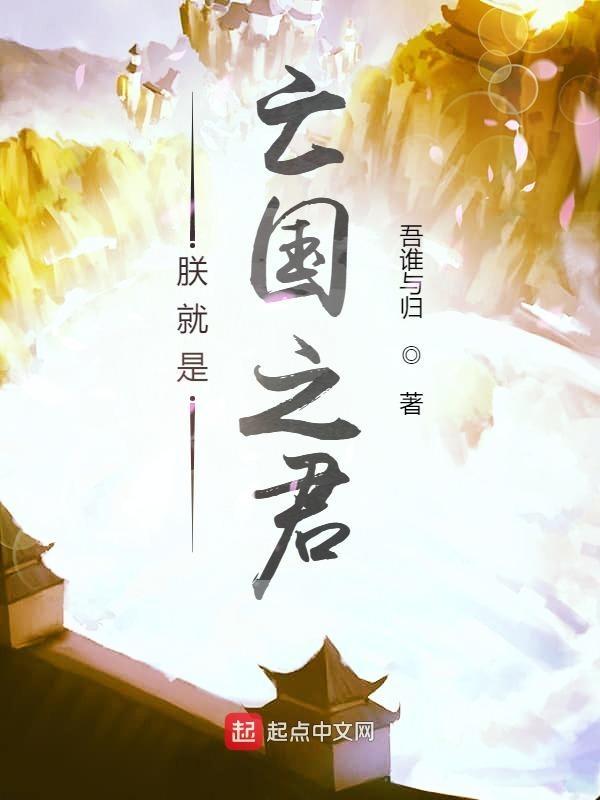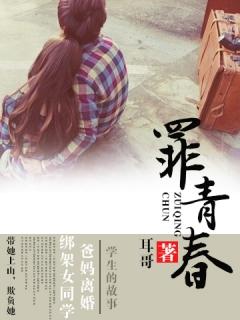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状元郎 > 第三六一章 谁是解元(第1页)
第三六一章 谁是解元(第1页)
衡鉴堂中,同考官们各自发表看法。
“礼房的文理更优!”
“诗房的才气更胜!”
“礼房的文章已有圣贤风采!”
“主考大人可是夸过诗房的文章,宛如东坡在世……”
结果十二位同。。。
夜阑人静,苏录独坐禅房,烛火摇曳如梦。窗外秋风拂桂,簌簌落英铺满石阶,宛如天降素雪。他手中仍握着那张写有“父病得安,儿不负志”的素笺,指尖轻抚字痕,仿佛能触到千里之外父亲微弱的呼吸与欣慰的笑意。
忽闻钟声三响,悠远沉静,自山巅古寺回荡而下,涤尽尘心杂念。苏录缓缓闭目,默诵《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此语如今听来,竟似萧提学低语耳畔,又似父亲咳喘间隙中的叮咛。十年寒窗,一朝成名,然荣耀加身之时,他心中所感非喜非傲,唯余敬畏??对命运之重、师恩之深、亲恩之切,皆不敢轻负。
次日清晨,慧明禅师遣小沙弥送来一封密函,乃萧提学亲笔。信中言道:“解元虽贵,不过仕途初阶。京师风云诡谲,新党旧臣角力不休,你文章锋芒内敛而意蕴深远,已动人心弦,恐为权要所忌,亦或为投机者所用。此后言行,须慎之又慎。待你进京会试,我当先行入京,为你暗布人脉,避祸趋吉。”
苏录读罢,久久不语。他知道,这封信不只是提醒,更是一道无形的枷锁??从此以后,他不再只是泸州苏家的子弟、昭觉寺中的学子,而是天下瞩目的“蜀中奇才”,一举一动皆牵动朝野目光。名望如衣,初时暖身,久则压肩。
正思忖间,门外脚步纷沓,苏满风尘仆仆而至,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兄长!家中来信,父亲昨夜已能起身进食,连太医都说‘此乃奇迹’!他说梦见你高中解元,含笑而醒,自此气顺神清。他还命我转告你一句:‘吾儿登科,胜服仙药百剂。’”
苏录闻言,眼眶骤热,强忍泪水,只低头合掌,喃喃道:“父亲安康,天地同庆。”
苏满坐下,饮了一口茶,又道:“可眼下麻烦也不少。泸州知府昨日派人至宅邸,说是奉上宪之意,欲邀你返乡巡游,受乡民叩贺;更有成都几位御史联名请宴,称要为‘川中第一才子’接风洗尘。这些人……怕不是真心敬才,而是想借你之名扬己之声望。”
“一律推辞。”苏录断然道,“我尚未进士及第,何敢以解元自居?况此番功名,实赖诸人成全??师父教诲、兄长奔波、弟弟侍疾、禅师护持,岂是我一人之力?若此时张扬炫耀,便是忘本。”
苏满点头称是,却又低声问:“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会试在明年春,路途遥远,是否先归家省亲再赴京?”
苏录沉吟良久,终摇头:“不可。一则父亲虽好转,仍需静养,我不宜扰其心神;二则此刻返泸,必被官绅围堵,徒增虚礼烦扰。不如暂留成都,继续研习经义,尤以《尚书》《周礼》为重,补我往日疏漏。待冬月启程北上,直趋京师,方能从容应对。”
话音未落,忽闻院外喧哗之声渐近。片刻后,小沙弥急步入内,神色慌张:“施主,外面来了数十人,打着‘恭贺解元公’旗号,有举人、秀才,也有地方士绅,说是要当面拜谒,题诗留念,已在山门前跪了一片!住持师父拦不住了!”
苏录皱眉,起身欲出,却被苏满一把拉住:“你这一露面,今日便不得安宁。这些人未必怀恶意,但一旦开了口子,明日就是官府出面,后日便是藩台大人亲临!你想清净修学,从此无望!”
慧明禅师此时缓步而来,手持佛珠,面色平静:“苏施主,老衲有一策,不知可否一听?”
“请禅师赐教。”
“你既已成名,避无可避。不如顺势而为,却不迎其势。今日本寺将举行‘秋祭超度法会’,专为战乱亡魂与久病逝者祈福。你可于法会上代父立牌位,焚香诵经,公开谢恩天地、师长、亲人。此举既显孝心,又避俗礼,且合佛门清净之道。众人见你虔诚低调,自然敬重,而不便强求相见。”
苏录眼前一亮:“妙极!如此既能表达心意,又不失本分。”
当即更衣易袍,换上素色布衫,随慧明禅师步入大雄宝殿。钟鼓齐鸣,梵呗响起,三百僧众列队而立,香烟缭绕如云。苏录捧牌位立于前,上书“先慈苏母李氏莲位”及“严父苏公讳某长生牌位”,双膝跪地,三叩首,声泪俱下:
“儿录不孝,久离膝下,幸赖天地垂怜,严父得延残喘。今日侥幸得中,非为荣身,实为承志。愿以此功德,回向双亲,祈寿康宁;并济苍生,不负所学!”
言毕,亲手点燃灵位前长明灯,火光跳跃,映照他清瘦面容,却透出一股凛然之气。殿外人群闻其言、观其行,无不感动落泪。有人低语:“此子不仅才高,更是至情至性之人。”遂无人再敢喧哗,纷纷合掌默祷,悄然散去。
一场风波,就此化解于无声。
自此之后,苏录更加谨言慎行。每日晨起诵经,午习《春秋》《礼记》,晚则与萧提学书信往来,探讨政局走势。他渐渐明白,真正的学问不在考场胜负,而在如何在这浊世之中守住一颗清明之心。
十月霜降,成都城外枫叶尽赤。一日午后,苏录独自漫步后山,忽见崖畔那株老梅竟又抽出新枝,枯木逢春,令人惊叹。他凝视良久,忽觉胸中豁然开朗,提笔回房,作《观梅悟道赋》一篇:
>“梅生于石罅,非择地而生,乃因志不移也。风霜愈烈,其香愈清;困厄愈深,其节愈坚。世人观梅,只见花开,不知其根扎于绝境,血渗于岩隙。君子处世,何异于此?功名如花,终将凋零;唯有守志如根,方可岁寒不改。”
此文后被慧明禅师抄录悬挂于禅堂,谓之“真儒之言”。
与此同时,京师消息陆续传来。内阁大学士张孚敬(张璁)主持朝政,推行新政,裁汰冗官,整顿科举,尤其严查各地乡试舞弊。四川虽远在西南,亦有数名考官被劾去职,唯独本次乡试因萧提学亲自督学、程序严密,得以保全声誉。朝廷特旨嘉奖,并点名提及苏录试卷“义理精纯,文风敦厚,足为天下士子楷模”。
更有意思的是,翰林院一位老学士读罢苏录《君子不器》一文,拍案叹曰:“此子有王阳明早年气象,惜乎生于今世!若在正德年间,必为心学大将!”此语传开,竟引得一批蛰伏多年的心学门人纷纷关注苏录,私下称其为“阳明再传之希望”。
然而,赞誉背后,暗流涌动。
十二月初,一名自称“江南游学士人”的男子夜访昭觉寺,求见苏录。此人姓陈名文渊,言谈儒雅,出口成章,自称曾受业于王阳明晚年弟子王畿门下,今闻苏录弘扬心学,特来切磋。两人论学一夜,从“致良知”谈到“万物一体”,彼此激赏。
临别时,陈文渊忽低声问道:“苏兄可知,当今圣上虽重科举,却忌心学?昔日阳明先生死后不得谥号,门人遭贬者无数。你文章处处暗合心学宗旨,若不明哲保身,恐难登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