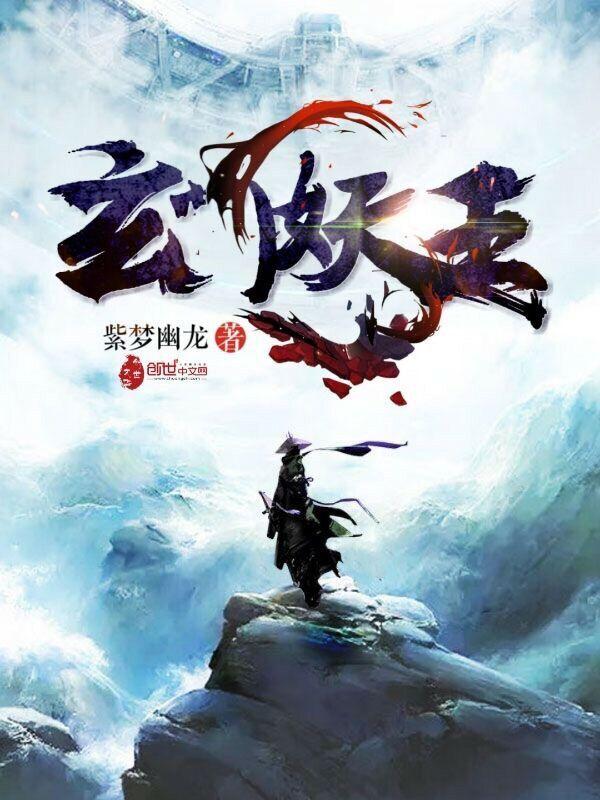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状元郎 > 第三四四章 反挖墙脚(第1页)
第三四四章 反挖墙脚(第1页)
苏录没正面回答夏邦谟,夏邦谟以为他当头当惯了,‘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一路上便没断了劝说。
“弘之兄,我知道你才高八斗,在泸州士子间独领风骚惯了,但人外有人山外有山。泸州太小了,比起成都重庆如何?。。。
夜色如墨,寒风卷着细雪扑打在青砖墙面上,发出沙沙的响声。临安城外三十里处的一座破庙中,火光微弱地跳动着,映照出三张神色各异的脸。
林昭盘膝坐在干草堆上,手中握着一卷残破的《春秋》,眉头紧锁。他身上的儒衫早已被雨水浸透,边缘泛白起毛,袖口还沾着泥点。可他的眼神却亮得惊人,仿佛能穿透这漫漫长夜,直抵天心。
“你说朝廷已下令通缉你?”赵砚之靠在墙边,声音低沉,“就因你在殿试策论中直言‘权相误国’四字?”
林昭没有抬头,只是轻轻翻过一页书:“不止如此。我还说,当今圣上若再纵容秦桧余党把持朝纲,不出十年,江南必乱。”
赵砚之倒吸一口凉气,忍不住站起身来:“你疯了!那可是参知政事王?的亲信幕僚写的奏章底稿,你竟敢原样抄进策文?还当着满朝文武念出来!”
“我不是抄。”林昭终于抬眼,目光如刀,“我是据实而书。那些话本就是百姓所言,我只是替他们说了出来。”
屋外风雪更急,吹得破窗咯吱作响。角落里一直沉默的沈清梧忽然轻笑一声:“所以你现在是天下士子心中的‘真状元’,却是朝廷眼里的钦犯。”
林昭望着跳跃的火焰,缓缓道:“我本无意功名。可既入考场,便不能昧良心答题。若连一个读书人都不敢说实话,这天下还有谁会说?”
赵砚之叹口气,从怀中取出一封密信:“这是我在礼部当差的师兄偷偷递出来的。今早内阁议决,原定放榜日推迟七日,理由是‘策卷复核未毕’。但真正的原因……是你那一纸策文震动宫闱,有人要压下你的名字,另立他人。”
沈清梧冷笑:“果然如此。听说吏部尚书李崇安的侄儿李元朗,这次也参加了殿试。成绩平平,却得了不少考官暗中赞誉。若非你横空出世,榜首怕早就内定了。”
林昭闭上眼,良久才道:“我不争虚名。但若他们连榜都不让我上,那就是欺天下人心。”
赵砚之压低声音:“我已经联络了几位同年,准备联名上书。只要我们能在放榜前将你的策文刊印散发,让万民共睹真相,看他们如何遮天蔽日!”
“不可。”林昭摇头,“你们一旦出头,便是同罪。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岂能让诸君陪我赴死?”
“你以为我们是为了你?”沈清梧忽然站起,眼中燃着怒火,“我们是为了这个国家!多少年了,科举成了权贵分赃的游戏,寒门子弟拼尽一生,最后只换来一句‘文章欠佳’!你这一篇策论,像一把刀,剖开了这腐烂的脓疮。现在你要让我们缩回去?让百姓再等下一个十年?”
林昭怔住。
火光映在三人脸上,忽明忽暗。
良久,林昭缓缓开口:“若要行事,必须快、准、狠。第一,找刻坊连夜雕版;第二,联络城中讲学社与书院学子,明日清晨于贡院门前集会;第三,派人潜入宫禁,设法将策文副本送至太常卿韩老大人手中??他是先帝旧臣,素有直声。”
赵砚之点头:“刻坊我熟,东市‘文渊阁’老板是我表舅,最是仗义。学生那边,我即刻写信,以‘观榜疑云’为题,煽动舆情。”
沈清梧则冷冷一笑:“至于进宫……我有个办法。明日乃冬至祭典,百官齐聚南郊。我可以混入乐工队伍,借献乐之机,将密信藏于琵琶腹中,交予韩大人贴身小童。”
林昭深深看了她一眼:“此去凶险万分,你何必……”
“因为我父亲也是被秦党陷害致死的御史。”沈清梧打断他,语气平静却带着彻骨寒意,“十五年来,我隐姓埋名,苦读诗书,就是为了等这一天。林昭,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三人相视无言,唯有风雪呼啸。
次日凌晨,天未亮透,临安城已悄然骚动。
街头巷尾,一种名为《殿试策惊雷录》的小册子悄然流传。封面墨迹淋漓,写着一行大字:“天下不可无直言之士,朝廷岂能掩万民之声!”内中全文登载林昭殿试策论,字字如剑,句句见血。尤其那句“权相虽亡,党羽犹存;奸佞不在台阁,而在人心”,被人争相抄录,贴满茶肆酒楼。
贡院门前,数百名身穿青衫的学子聚集,手持白幡,上书“还我公道”“真才须上榜”等字样。他们并非哗变,而是静默跪拜,每人面前摆放一支点燃的蜡烛,在寒风中摇曳不灭。
巡城司欲上前驱赶,却被人群中的老秀才拦住:“我等皆系国家养士,今日只为求一个道理。若连说理之地都没有,还要这科举何用?”
消息传入宫中时,正值早朝。
宰执大臣王?面色铁青,将一份《惊雷录》摔在地上:“查!给我彻查是谁泄露策卷!还有这些闹事的学生,全部记档除名!”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臣拄杖而出,正是太常卿韩允衡。他颤巍巍拾起策文,朗声道:“老臣以为,不必查了。此文出自新科进士林昭之手,光明磊落,掷地有声。若说泄露,不如说是天意使然,让天下人听见了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