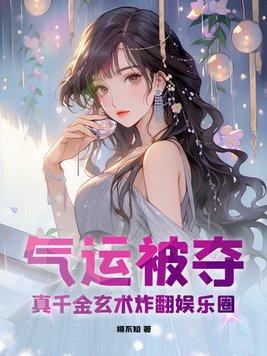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大唐腾飞之路 > 2043 吴有道(第2页)
2043 吴有道(第2页)
风掠过荒漠,卷动书页。阿勒泰低声念完,将书投入火中。
火光中,他仿佛看见十年前的自己,背着这本笔记穿越戈壁,饥寒交迫,却始终不肯松手;又似见柳芸在东市灯下逐字誊抄,裴景衡在朝堂冷笑拂袖,李恒在初问亭外仰望苍天……无数面孔在他眼前流转,最终定格在那个盲童脸上??手持冰块,眸如星辰。
“老师,”他喃喃,“你说问题不需要墓碑。可若连提问的人都被抹去,谁还记得你曾存在过?”
翌日清晨,阿勒泰召集周边戍卒、流民、商旅百余人,立于废墟之前。
“这座屋,他们烧了一次。”他站在高处,声音不高,却清晰可闻,“还会烧第二次、第三次。但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说出真相,它就会建起来第七次、第八次,直到再也烧不尽。”
人群中有人抽泣,有人握紧拳头。
“我不需要官府批准,也不求朝廷拨款。”他继续道,“我要你们每一个人,轮流来这里值守一天。写下你听到的故事,收下别人不敢公开的信。我不强求你们冒死,但请记住:当你选择沉默时,黑暗就赢了一寸。”
一名年轻戍卒站出来:“我守第一天。”
接着是牧羊老人:“我守第二天。”
一个带着孩子的妇人颤声道:“我丈夫去年死在屯田营,没人给说法。我守第三天。”
一百零七人依次上前签名,用炭、用血、用指甲划在一块木板上。阿勒泰命人将其竖立原地,作为新屋基石。
七日后,新的“安西听屋”落成。四根胡杨木柱撑起茅草顶,墙上挂着一面从敦煌运来的铜鼓,鼓面刻着四个大字:“仍可发声”。
与此同时,长安皇宫内,太子李恒正伏案疾书。他已连上三道奏折,请求设立“独立问政司”,直属皇帝,不受六部节制,专司监督各地听屋运作及落实公询决议。然而每一道都被尚书令压下,理由是“权出多门,恐乱纲纪”。
这一夜,他召见柳芸。
“你可知裴景衡昨日死了?”李恒望着烛火,语气沉重。
柳芸一震:“怎么死的?”
“风沙迷途,仆人寻到时,尸体已被黄沙半掩。怀里只剩半块干饼,和一张写满悔恨的纸??他说,若有来世,愿做个记录真相的小吏,而非执掌权柄的大臣。”
柳芸久久无言,终是叹息:“他终究明白了。”
“可活着的人还没明白。”李恒冷笑,“户部尚书昨日竟提议,将‘轮值问政’纳入科举考试内容,让士子背诵‘如何回答百姓提问’!他们根本不懂??问政不是表演,是权力向人民低头。”
柳芸眸光一闪:“那就让他们亲眼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问政。”
她取出一份地图,摊开于案??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全国一百零七座已建成或筹建中的听屋位置,红线串联,竟隐隐构成一幅巨网,覆盖大唐疆域。
“我们准备在明年春分,举行‘百屋同问’。”她声音坚定,“一百零七地同时开启公询,议题不限,形式自定,全程记录,互派代表观礼。届时,我们将把所有问答汇编成册,命名为《元和百问录》,直送御前,并抄送各藩镇、节度使、乃至吐蕃逻些城。”
李恒动容:“若是成功,便是百年未有之壮举。”
“若失败,”柳芸淡淡道,“也足以证明,有些人宁可毁掉制度,也不愿放弃谎言。”
消息传出,朝野震动。支持者奔走相告,称“民心可聚”;反对者则暗中串联,扬言“必使其流产”。
而在岭南某县,一名县令接到密令后,连夜召集心腹:“明日午时,有一批‘访察使者’途经本境。据报,为首者乃成都诘灵台陈砚。务必……让他问不出一句话。”
夜雨淅沥,打湿了驿道泥泞。一辆马车缓缓驶入山谷,车内坐着陈砚与两名同伴。突然,前方滚石落下,堵住去路。未等反应,四周火把亮起,数十黑影包围而来。
“你们是什么人?”陈砚厉声质问。
为首者冷笑:“奉命清理聒噪之徒。”
刀光闪动,惨叫划破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