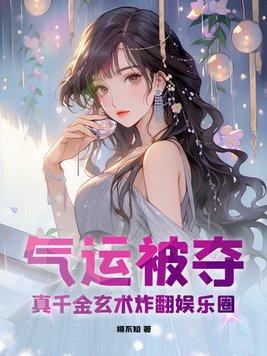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大唐腾飞之路 > 2043 吴有道(第3页)
2043 吴有道(第3页)
然而三日后,同一地点,又有三人徒步而来。为首女子摘下面纱,正是柳芸。
“你们杀了陈砚?”她平静地问。
一名俘虏跪地颤抖:“小人……只奉命行事……”
“我知道。”柳芸点头,“我也知道幕后是谁。但我今天不杀人,也不报官。”
众人愕然。
她从怀中取出一本薄册,递给随行文书:“记下来??元和五年正月初九,岭南道某县,发生‘噤声事件’:三名诘灵台成员遇袭,一人殉职,二人重伤。凶手自供受县令指使,目的为阻止‘百屋同问’调查。现已捕获七人,其余在逃。”
文书奋笔疾书。
柳芸又道:“把这份记录送往最近的听屋,刻印五百份,沿途张贴。再派人快马加鞭,送至长安、洛阳、扬州、成都、敦煌……每一座筹建中的听屋门前,都要贴一张。”
她转身离去,留下一句话:“你们可以杀一个人,但杀不死一个问题。”
春风解冻之时,大唐各地悄然兴起一股“筑屋潮”。农闲时节,村民们自发集资建屋,工匠义务献工,学子自愿值守。有的地方没有鼓,便挂一口破钟;没有纸笔,便用木片刻字;没有屋顶,就拿牛皮遮雨。
而在吐蕃逻些城,首座“雪域听屋”已在布达拉宫脚下落成。赞普亲自敲响静听鼓,宣布第一条法令:今后凡官员述职,须先回答三问??百姓吃得饱吗?穿得暖吗?敢说话吗?
大唐使者回禀,皇帝听罢,久久凝视殿外梨花盛开,忽叹曰:“朕治天下多年,以为威仪足以服人,赋税足以养民。今日方知,最高贵的统治,是肯弯腰倾听。”
元和五年春分,晨钟响彻九州。
一百零七座听屋simultaneous开启大门。农民问粮价,士兵问军饷,学子问科举,寡妇问抚恤……问题如春雷滚滚,震动山河。
敦煌莫高窟前,阿勒泰再次站上讲台。孩子们围坐四周,练习书写新的句子:
“我可以问吗?”
“你会听吗?”
“我们能改变吗?”
夕阳西下,金光照亮千佛洞万千佛眼。仿佛整个天地都在倾听。
那一夜,觉远在第172窟壁画背面添上最后一笔题记:
>“百屋同问,万口齐声。
>鼓未绝,火不熄,问不止。
>后之来者,若见此壁,
>请俯身一听??
>土中仍有心跳。”
地下深处,那块晶石忽然光芒大盛,持续整整一夜,而后归于沉寂。
据说,那一晚,全大唐有十七个婴儿出生时紧握拳头,掌心皆有一道细纹,形如“问”字。
风仍在吹。
它穿过废墟,掠过新城,拂过少年睁大的双眼。
带着一个问题,奔向未知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