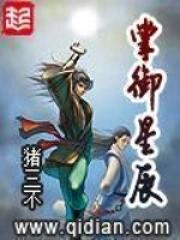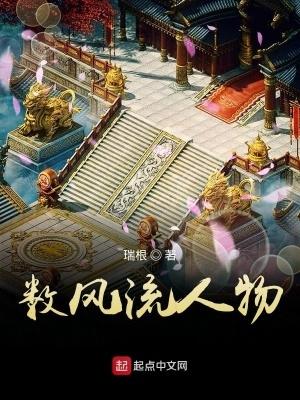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大唐腾飞之路 > 2043 吴有道(第1页)
2043 吴有道(第1页)
“姓宋的!我知道你在里面!出来!”
就在宴席已近尾声时,酒楼外,一个突兀的声音却在冷寂的大街上响了起来。
风自西域来,卷着黄沙与驼铃声,越过玉门关的残垣断壁,吹入敦煌城内。街巷间已有孩童口诵“三问”??一问粮足否?二问税轻否?三问官惧民否?这是阿勒泰在莫高窟前教下的第一课,如今已如野火燎原,烧进了边陲百姓的心里。
那夜觉远题记落笔不久,第172窟便迎来一位不速之客。他身披褐袍,头戴斗笠,脚上草履破旧不堪,却步履沉稳。守夜的小沙弥欲拦,却被其手中一枚铜牌止住??正是柳芸所执“盲评令”的复刻版,由皇帝特许分铸十枚,专供诘灵台要员通行关隘。
来人摘下斗笠,露出一张清癯面容,双目深陷,却炯炯有神。他是成都诘灵台主事之一,姓陈名砚,本是药铺学徒出身,因揭发地方官虚报药材用量而遭构陷入狱,后经柳芸营救脱险,自此投身公询之事。此番千里跋涉,只为亲见阿勒泰一面。
“您可知我为何而来?”陈砚跪坐于蒲团之上,声音低哑,“琼州青莲再生,吐蕃求设听屋,天下皆言‘问政兴’。可就在三日前,我在眉山查案时,发现一县令竟将‘轮值问政’改为‘代民作答’??百姓不来,便由衙役假扮乡老,围坐堂前,演一出‘万民称颂’的戏。”
阿勒泰默然良久,只取炭笔在石板上写下两个字:“再问。”
“可他们已不敢问了。”陈砚苦笑,“有人夜里投书被截,次日全家失踪;有人击鼓三次,第四次再去,鼓已被搬走,说‘扰民不安,暂行禁鸣’。我们送去的《汇要》抄本,在有些地方成了违禁之物,藏一本杖八十,传一本流三千里。”
灯影摇曳,映照壁画上的“持冰者”。那孩童眼神清澈,仿佛正凝视着眼前这两位为真相奔走的人。
“所以您得回去。”陈砚直视阿勒泰,“不是以使臣身份,不是以钦差名义,而是以一个普通人,重新踏上这条路。您若隐退,静听屋就成了庙里的塑像,供人祭拜,却不再说话。”
阿勒泰未答,只是起身推开窗棂。月光倾泻而入,照亮墙角一只陶瓮??那是他从长安带回的泥土,混着终南山初问亭下的雪水、东市茶肆门前的尘灰、还有李砚当年流放途中饮过的凉州井盐。他曾答应自己:只要这土未干,他就不能真正停下脚步。
“我不是不愿回。”他终于开口,声音如风穿隙,“我是怕我一出现,人们又会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们要建的不是英雄的时代,而是人人敢问的年代。”
陈砚闻言动容:“可现在,许多人连‘问’这个动作都快忘了。他们开始习惯沉默,就像十年前一样。只不过那时是因为恐惧,现在……是因为疲惫。”
话音未落,门外忽传来急促脚步。一名年轻僧人捧着一封火漆密信奔入:“师父!凉州急报??安西听屋昨夜遭焚!两名值守老兵重伤,一人临终前留下血书两字:‘闭嘴’!”
满室死寂。
觉远缓缓合掌,低声诵经。阿勒泰却猛地站起,抓起墙边竹杖,大步向外走去。
“你要去哪?”陈砚追出。
“安西。”他头也不回,“既然他们烧了屋子,我就再盖一座。既然他们想让人闭嘴,我就教更多人开口。”
三日后,阿勒泰孤身抵达安西故城。昔日烽燧旁,焦木横陈,残垣犹带烟痕。两名老兵躺在临时搭起的草棚中,一人昏迷不醒,另一人手臂缠满布条,见阿勒泰到来,挣扎欲起。
“不必。”阿勒泰按住他肩膀,目光扫过地上尚未完全烧尽的纸片??那是百姓投书的残页,依稀可见“屯田欠饷”、“戍卒冻毙”等字。
他蹲下身,轻轻拾起一片灰烬,放入随身布袋。
“是谁干的?”他问。
老兵喘息道:“黑衣……无面……半夜突至……砸鼓、焚屋、打人……临走说……‘从此无人可问’……”
阿勒泰闭目片刻,忽然问道:“你们还愿重建吗?”
老兵愣住,随即用力点头:“只要您肯来,我们就敢守。”
当夜,阿勒泰独自登上附近沙丘,点燃一堆篝火。他取出那包灰烬,撒入火中。火焰骤然腾起,映红半边天空。
他盘膝而坐,取出随身携带的《问北录》原本,翻开最后一页。那是李砚的手迹,字迹潦草却力透纸背:
>“吾行万里,唯见一病:上不知下苦,下不信上能改。故政不通,民不聊生。
>然则解法亦简??令上有耳,下有口,上下相闻,则病自愈。
>若一日无人敢问,则国虽存,实已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