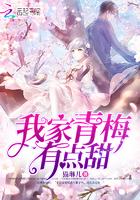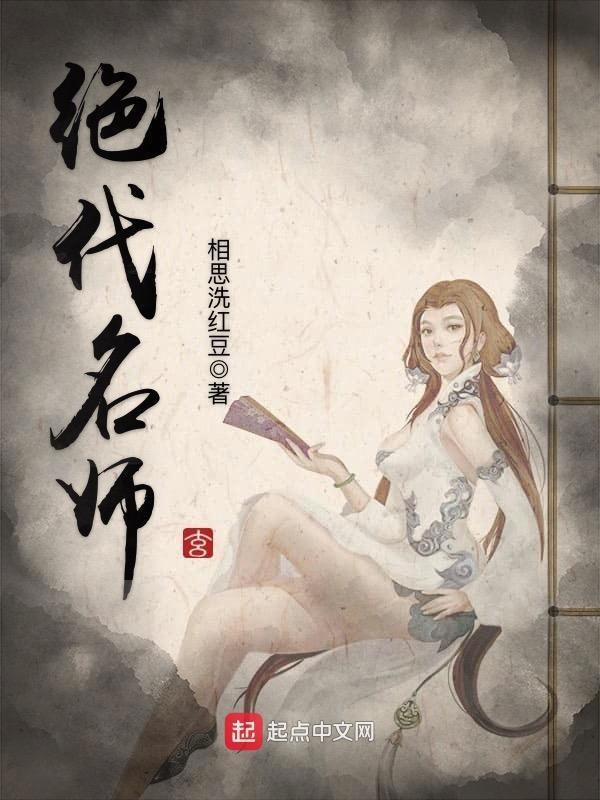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大唐腾飞之路 > 2042 留字(第2页)
2042 留字(第2页)
数日后,敦煌莫高窟第172窟内,觉远老僧正用毛笔小心翼翼修补壁画上的文字。那句“问题从不高高在上,它匍匐于泥土之中,等待一双肯弯下的耳朵”已被重新描金,墨香未散。门外传来脚步声,他回头,看见阿勒泰背着竹篓走来,脸上风尘仆仆,眼中却清明如泉。
“你来了。”觉远微笑。
“我回来了。”阿勒泰放下行李,目光落在壁画上,“它还在听吗?”
“每夜三更,风穿过窗棂,我都听见画中人在低语。”觉远指着角落一处新绘的小像??是个孩童,手捧冰块,眼神清澈,“这是新添的,名叫‘持冰者’,纪念那位盲童。”
阿勒泰怔住,随即躬身合十。
当晚,两人共坐灯下,翻阅各地送来的《公询后续录》。忽有弟子匆匆奔入:“师父!琼州来信,说李承业坟头长出一株青莲,三年枯死,今春复生,花开七瓣!”
觉远抚须不语。阿勒泰却起身走到洞外,仰望星空。北斗七星清晰可见,其中天权星格外明亮??那是李砚生前最爱指给他看的一颗星。
“老师,”他轻声说,“你听见了吗?他们开始问了。”
风过千佛洞,万龛齐鸣,宛如回应。
半月后,一则消息震动朝野:吐蕃赞普遣使求见大唐皇帝,携国书一封,提出三项请求??
其一,请派诘灵台使者赴逻些城,指导设立“雪域听屋”;
其二,愿开放唐蕃古道,允许两国百姓自由往来陈情;
其三,提议每岁冬至,两国同时举行“反问日”,官员共答三问,互派监礼使观礼。
皇帝览毕,大为震动,召集群臣商议。有人反对,称“夷狄难化,此举恐损天威”;亦有保守派讥讽“效仿匹夫喧哗,岂是治国之道”。唯有太子李恒力排众议:“若真理不分华夷,则倾听亦不应有边界。今日我们教他们问,明日他们也会教我们听。”
最终,皇帝准奏,并下诏曰:“自今以后,凡属藩邦愿行‘公询之道’者,大唐皆以礼相待,赠《问北录》一部,授静听鼓一面,助其立屋建制。”
诏书传至敦煌,阿勒泰正在教一群孩子写字。他们围坐在窟前空地,用炭条在石板上练习“问”字。一个小女孩写了几遍都不满意,皱眉道:“这个字好难,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弯?”
阿勒泰蹲下身,握住她的手,一笔一划重新写下:“因为问题从来不是直的。它要绕过谎言,穿过恐惧,跨过沉默,才能抵达真心。所以它必须曲折,但也正因如此,它才走得远。”
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忽然抬头:“阿勒泰爷爷,我们会一直能这样说话吗?”
阿勒泰望向远方,夕阳正沉入鸣沙山,金光洒满千佛洞。他轻声道:“只要你们不忘记提问,就没人能堵住你们的嘴。”
夜幕降临,第172窟内的油灯再次点亮。觉远在壁画下方添了一行新题记:
>“元和四年冬,天下大询始成。
>百姓开口,官俯首听。
>鼓声百零七,非止哀亡魂,亦唤生者醒。
>是知:国之兴,在于民敢言;
>民之勇,在于上有容。
>此谓??
>**问则存,塞则亡。**”
与此同时,终南山巅的初问亭遗址上,那块无字碑前不知何时多了一尊小小的陶鼓。每逢月圆之夜,山风穿谷而过,鼓面便会微微震颤,发出几不可闻的嗡鸣,仿佛有人在遥远的未来,轻轻敲了一下。
而地下深处,那块晶石的光芒仍未完全熄灭。它像一颗沉睡的心脏,缓慢搏动,等待下一个愿意弯下腰去倾听的人。
风继续吹过大唐的每一寸土地。
在田埂上,在军营中,在学堂里,在市井间……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性地问一句:
“这事,该不该?”
“这话,能不能说?”
“这路,还能走吗?”
没有人规定他们必须得到答案。
但仅仅提问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觉醒。
问题不死。
因为它从未真正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