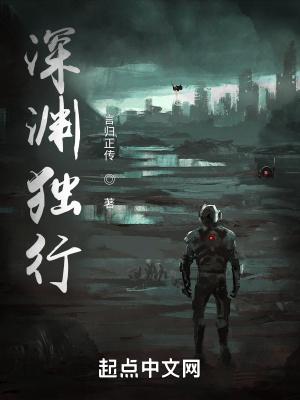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大唐腾飞之路 > 2042 留字(第1页)
2042 留字(第1页)
这云山县城看起来并不大,但带给萧寒等人的感觉,却是异常的祥和。
此时,夕阳已落,在最后一丝晚霞的映衬下,城中处处都是白色的炊烟飘起。
终南山的雪,终于在公询会结束后的第七日停了。晨光初照,山脊如银刃劈开云层,将一道清冷的光辉洒向长安城南的静听屋旧址。那间漏雨的草棚早已被拆去,原地立起一座青瓦白墙的小院,门楣上悬着一块无字匾额,据说皇帝曾亲笔题写“民声所寄”四字,却被阿勒泰婉拒:“声音不在牌匾上,而在人心中。”
院内石鼓犹存,鼓面斑驳,裂纹如蛛网蔓延,却仍能发出沉稳的回响。每日清晨,总有百姓自发前来击鼓,不为诉冤,只为告诉这个世界??我还敢说话。
而此时,阿勒泰正坐在初问亭外的石阶上,手中捧着一碗粗茶。茶色浑浊,是他从山下一位老妪那里讨来的野菊泡制,入口苦涩,却有一股暖意直透肺腑。他望着远处蜿蜒入城的官道,那里仍有红签飘扬,虽已不如百日前那般汹涌,但细流不断,像是大地深处不肯干涸的血脉。
“你真要走?”太子李恒的声音自身后传来,带着几分压抑的痛楚。
阿勒泰没有回头,只轻轻吹了吹茶面浮沫:“我来时无名,去时亦不必留痕。”
“可你改变了大唐。”李恒走近几步,紫袍垂地,靴底踏碎了一片残雪,“父皇说,这是百年未有之变局。而你是引火之人。”
“火种本就在。”阿勒泰终于转头,目光温和,“我只是掀开了盖子。”
李恒蹲下身,与他对视:“那你为何不留下来?朝廷需要你,百姓信你,连西域诸国都在打听‘咨政使’何时出使……你若愿掌都察院,我可力荐;若想入阁议政,我也……”
“殿下。”阿勒泰轻声打断,“权力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它能杀人,而是它能让一个人忘了自己为何出发。”
他指向山下:“你看那些持红签的人。他们不怕官差,不怕权贵,甚至不怕死,因为他们终于相信,一句话也能撼动江山。可若有一天,我说的话成了圣旨,我的沉默就成了禁令??那时,静听屋就该烧了。”
李恒怔住,良久才低声道:“你就这么不信我们?”
“我不是不信你们。”阿勒泰站起身,将空碗放在石台上,“我是太信百姓了。所以我不能留下。一旦我成了‘大人’,他们就会仰望我,而不是平视彼此。他们会等我说话,而不是自己开口。那样,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风掠过山巅,卷起他宽大的袖口,露出手腕上一道陈年疤痕??那是十年前在乌兰察,他被酷吏鞭打后留下的印记。他曾用这双手埋葬过七十三具尸体,也曾握笔写下第一份《问北录》。如今,它们只是静静垂落,仿佛承载过太多重量,反而变得轻如鸿毛。
李恒忽然问道:“那李砚呢?你说他是你的老师。可我查遍史籍,竟无此人记载。”
阿勒泰笑了,眼角皱纹如刀刻:“因为他从没想过被人记住。他活着的时候,只是一个驿站小吏,因直言关中旱情被杖责三十,流放凉州。他在路上写了三十七篇札记,叫《问北录》,最后一篇写完那天,他饿死在戈壁滩上,怀里还揣着半块干饼,留给同行的孩子。”
他顿了顿,声音渐低:“后来我找到了那本笔记。他说:‘问题不会死,因为它不需要墓碑。只要还有人觉得不公平,它就会醒来。’”
李恒久久无言,最终只问了一句:“你会去哪儿?”
“回敦煌。”阿勒泰望向西方,“觉远师父还在守窟。我想去看看那幅《众生问答图》,问问它,是不是真的听见了人间的哭声。”
两人默然相对,直至日影西斜。
同一时刻,长安城东市的一处茶肆里,柳芸正低头整理一册厚厚的文书。她身边坐着几位来自各地诘灵台的代表,皆是普通百姓:洛阳的织妇、成都的药铺学徒、扬州的船工、凉州的牧羊人。他们围坐一圈,面前摊开着《元和公询汇要》的抄本,正在逐条核对建议落实进度。
“户部已下令彻查仓粮亏空,三个州府的转运使被罢免。”柳芸翻到一页,笔尖轻点,“但‘轮值问政制’推行受阻,尚书省以‘平民无知,恐扰朝纲’为由,暂缓施行。”
“那就再问。”织妇冷冷道,“去年我们不敢说话,现在敢了。他们怕的不是我们无知,是怕我们知道太多。”
众人点头。药铺学徒忽然抬头:“听说岭南那边,有县令开始伪造‘自愿签署无灾书’,逼百姓按手印?”
柳芸眸光一凛:“已有三起上报。我已命成都诘灵台派人暗访取证,一旦属实,立即启动‘血证公示’程序。”
“可裴景衡都倒了,怎么还有人敢这么干?”船工愤然拍桌。
“因为根还在。”柳芸缓缓道,“一个宰相倒下,不代表谎言的土壤消失。只要升迁靠的是‘太平景象’,只要考核看的是‘祥瑞数量’,就永远有人愿意粉饰太平。”
她合上文书,环视众人:“所以我们的事还没完。公询会结束了,但诘灵台必须活下去。我要在全国设一百座‘常驻听屋’,每座由五名平民轮值主持,接受匿名投书,每月汇总直报京师。你们,愿不愿意继续?”
“愿意!”五人齐声应答。
夜深人静时,柳芸独自走出茶肆,抬头望月。她摘下面纱,露出一张清瘦却坚毅的脸。十年来,她始终记得母亲临终前的话:“芸儿,你要替我说话。我不识字,但我看得见苦难。”
她取出怀中一枚铜牌,上面刻着“盲评令”三字。这是皇帝特许诘灵台使用的凭证,可直达御前。她摩挲良久,终究没有递出。有些事,必须靠民间自己走下去。
与此同时,在安西流放地的荒漠边缘,裴景衡正拄拐前行。风沙割面,昔日锦衣玉食的宰相如今衣衫褴褛,随行仅有一名老仆。途经一座废弃烽燧时,他忽然停下脚步,望向东方。
“您在看什么?”老仆问。
“长安。”他喃喃,“我在想,当年若听了那个小吏的奏报,会不会不一样?”
老仆苦笑:“可您当时说,‘民心易乱,不可轻信’。”
裴景衡闭目,泪水混着沙粒滑下脸颊:“我以为秩序高于一切。可现在才明白,真正的秩序,是让每个人都能说出真相而不被惩罚。我错了……错得彻骨。”
他从怀中掏出一本破旧账册,正是当年压下的灾情报表原件。他颤抖着将其投入篝火,看着火焰吞噬那一行行触目惊心的数字,仿佛烧去了最后一丝执念。
火光映照下,远处沙丘忽然闪过一点微光。那是新近设立的“安西听屋”,两名戍边老兵正轮流值守,记录一名流民的陈情。裴景衡凝望良久,终是一声长叹,转身走入风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