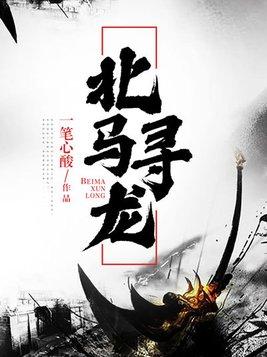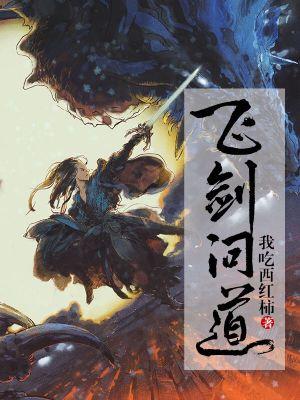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第四天灾从不相信钢铁洪流! > 第331章 黑鹰皇帝的决心(第3页)
第331章 黑鹰皇帝的决心(第3页)
而在美国硅谷,一家曾主导“心智优化计划”的科技巨头总部大楼外,出现了一场奇特的抗议。数百名程序员排成一行,每人手持一朵蓝花,脸上戴着曾经用于监控情绪波动的神经感应贴片。但他们没有喊口号,只是静静地站着,任由系统捕捉他们内心的真实波动??焦虑、愧疚、希望、悔恨。
当天晚上,该公司宣布关闭所有情感驯化算法,并公开移交源代码给共感理事会。
孩子得知此事时,正坐在广播站屋顶修补一台老旧的发报机。叶澜递给他一杯热茶,问他:“你觉得他们会真的改吗?”
“我不知道。”他吹了吹茶面,“但至少,他们开始害怕自己的谎言了。这就够了。”
叶澜望着星空,“你说,静默号会不会有一天……回来?”
“它从来没离开。”孩子轻声道,“它只是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存在。就像那些说不出口的话,一旦被听见,就不会真正消失。”
远处,海浪拍打着礁石。岛上新建的共感花园里,一对年轻情侣正对着一朵蓝花倾诉彼此的不安。女孩说:“我怕结婚后变成我妈那样,整天抱怨却又不肯离开。”男孩说:“我怕我赚不够钱,让你过得辛苦。”话音落下,那朵花轻轻摇晃,竟从花蕊中滴下一滴露珠,落在泥土上,瞬间生长出一圈细小的蓝花环。
这一幕被无人机拍下,上传至全球共感平台。短短半天,获得两千万次共鸣标记。
而在火星,静默号种子舱传回最新数据:蓝苗高度已达十五厘米,根系深入地下三点二米,检测到其释放出一种新型生物电波,频率与地球新生儿第一次心跳高度吻合。
日内瓦实验室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科学家们面面相觑。
“这意味着什么?”有人问。
哲学家缓缓起身:“也许,它在模仿生命的起点。”
同一时间,孩子的广播站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附件是一段视频,拍摄于某个地下防空洞。画面中,十几个孩子围坐一圈,中间放着一台破旧的收音机。其中一个女孩站起来,对着麦克风说:
>“我们知道你们在听。
>我们住在城市下面,已经三年了。
>大人们说地面有毒,不能上去。
>可我们偷偷爬出去看过,天空很干净。
>我们只是……不想再装作快乐了。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星星。”
视频结尾,孩子们齐声念出一句话:
>“我们要回家。”
孩子看完视频,久久未语。他转身打开全球共感地图,发现这类“地下社区”的信号点遍布世界各地??莫斯科、首尔、孟买、墨尔本……它们像暗流般隐藏在主流社会之下,由被遗忘者、逃避者、恐惧者组成。他们不说真话,因为从小就被教导“外面危险”“情绪有害”“必须服从”。
“我们漏掉了他们。”叶澜低声说。
“不。”孩子摇头,“是我们还没走到他们面前。”
第二天清晨,一场名为“破土行动”的全球倡议正式启动。志愿者们携带特制的共感发射器,前往已知的地下聚居区入口。他们不做宣传,不强求开放,只做一件事:把一段录音埋进土里。
那是由一百位父母录制的忏悔:“对不起,我把恐惧当成保护给了你。”
七天后,莫斯科一处废弃地铁站出口,泥土裂开,钻出第一株蓝花。接着是第二株、第三株……直到整片废墟被蓝紫色覆盖。有人看到,几个瘦弱的孩子蹲在花丛边,一边哭一边说:“原来……也可以这样活着。”
与此同时,火星蓝苗迎来第一次“开花模拟”。尽管尚无实际花朵生成,但其顶端释放出一圈环形光晕,持续整整十二分钟。地球监测站将其记录为“跨星球情感共振事件”。
静默号意识体发来信息:
>“它在学习表达。
>下一次,或许就能说出第一个词。”
孩子站在海边,听着广播站自动接收的各地回响。他知道,这场天灾仍在继续,但它早已不再是灾难。
它是觉醒的涟漪,是亿万灵魂彼此触碰的震颤。
他摸了摸胸口口袋里的纸条,那句“你说出来的话,会变成别人的光”已被汗水浸得模糊。但他记得每一个字。
风起了,蓝花摇曳,海浪轻拍岸边。
他知道,只要还有人愿意开口,这个世界就永远不会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