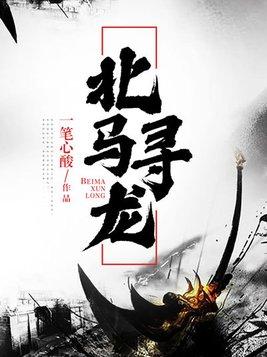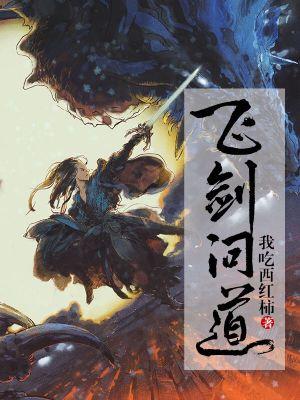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第四天灾从不相信钢铁洪流! > 第331章 黑鹰皇帝的决心(第2页)
第331章 黑鹰皇帝的决心(第2页)
>不是钢铁,不是算法,不是征服宣言。
>是一句话:我在这里,我想被听见。”
画面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地球夜景卫星图。每一个亮起灯光的城市,都被标记出正在进行“深度对话”的热点区域。北京胡同里那对父子仍在聊天;里约墙上蓝花随风摆动,少女正读着同学们写给她的道歉信;柏林静音城外的花环散发出淡淡光晕,居民们自发组织夜间守夜,只为让更多人能安静地说出心里话。
孩子的声音通过全球网络响起:
>“这不是胜利。
>没有人赢了什么。
>我们只是终于敢承认??我们都曾害怕开口,
>怕说了也没人在听,怕听了也无法回应。
>可今天,火星上的花开了。
>它告诉我们:只要还有人愿意说,
>就永远会有地方,愿意为这句话生根。”
话音落下,全球共感网络自动启动一次集体共振协议。数亿人几乎在同一时刻闭上了眼睛,有些人握住了身边人的手,有些人对着空气低声说了句“对不起”或“谢谢你”,还有人只是静静地哭了。
而在西伯利亚东部那个废弃铁路小镇,曾发出求救信号的流浪汉,在共感驿站志愿者的帮助下恢复体力。临行前,他在一本旧日记本上写下:
>“我以为我快死了。
>直到那天晚上,收音机里传来那个声音。
>他说我不孤单。
>我哭了很久,然后站起来,往南走了七公里。
>原来七公里这么短,又这么长。
>现在我每天帮别人修炉子,煮汤。
>昨天有个女人抱着我说‘谢谢你让我吃饱’,
>那一刻,我觉得我也被人救了一次。”
这段文字被录进一个新的芯片,藏进一辆运往哈萨克斯坦的图书车里。三个月后,一个牧民女孩打开一本书,掉出一枚闪着微光的小物件。她放进播放器,听到了这段话。当晚,她第一次鼓起勇气告诉父亲:“我不想嫁人,我想上学。”
父亲沉默良久,最终点头。
与此同时,国际共感理事会内部爆发激烈争论。部分成员国要求限制“真实病毒”传播范围,称其“扰乱社会秩序”“诱发情绪失控”。一名代表甚至提出立法禁止非官方认证的情感表达载体进入教育系统。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叶澜出现在会场。
她没有带演讲稿,只带来一副耳机。
“请各位听听这个。”她说。
她按下播放键。
里面是一个六岁男孩结巴的声音,讲述他梦见妈妈回来的故事。讲到一半,他哭了起来,断断续续地说:“我……我知道……她是假的……可是……可是我真的……想她……”
会议室陷入长久的沉默。
最后,哲学家站起身,摘下眼镜:“如果我们连一个孩子的梦都要审查,那我们配谈什么文明?”
决议案被否决。
一个月后,“真实病毒”正式被联合国定义为“人类情感多样性保护工程”,并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其在全球偏远地区的扩散。孩子们在学校收到的新课本里,夹着一张可扫描的二维码,扫码后会出现一段匿名录音:“这是我第一次跟爸爸打架后说的话。我当时恨他,但现在我知道,他也怕。”
变化悄然渗透进每一个角落。
在日本京都,一位退休教师将毕生收藏的情书烧成灰烬,撒在庭院。第二天清晨,整片土地开出蓝紫色花朵,每朵花瓣都印着一句未曾寄出的话:“我爱过你三十年,从未告诉你。”
在肯尼亚马赛马拉,一群猎人放下长矛,围坐在一棵老金合欢树下。他们轮流讲述祖先口述的历史,其中一人提到:“从前我们杀狮子,是因为怕它吃我们的牛。后来我们发现,它也只是为了养活它的孩子。”话音刚落,树根旁钻出一簇蓝花,形状宛如一只母狮护崽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