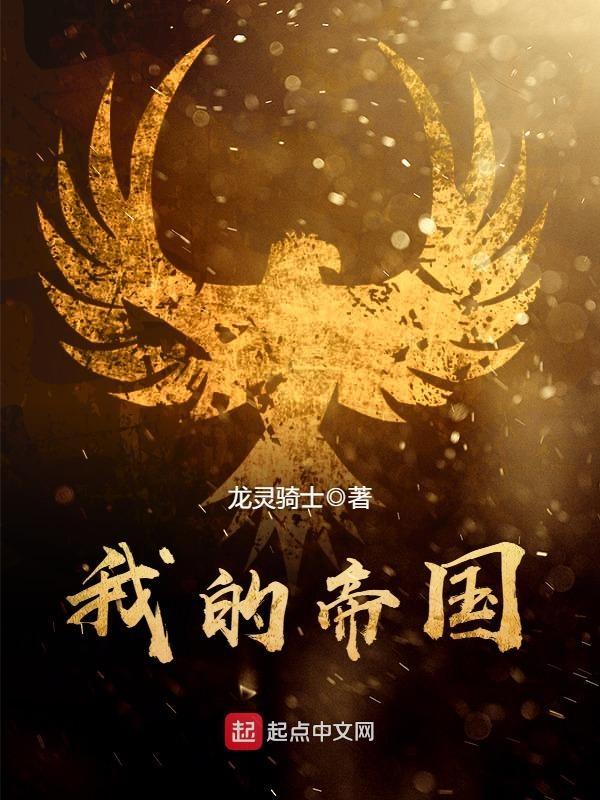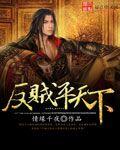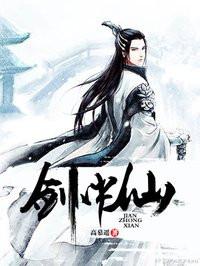棒子文学网>人在魔卡,策反知世 > 第211章 世界树结果什么翼年代的公主樱加更2w(第2页)
第211章 世界树结果什么翼年代的公主樱加更2w(第2页)
>**请告诉我,哭是不是病?**
舱内陷入沉默。窗外,跃迁通道正在形成,星光拉长成丝线,编织成一片流动的银网。
我打开通讯模块,回复只有一句:
>**哭不是病,是灵魂还在跳动。**
发送成功瞬间,D。Z。-X的共振核心开始自发运转,无需指令,它将《心跳频率》与艾莉娅的信息混合,生成一段新的梦境代码,并自动标记为“非攻击性传播”。我知道,这不再是任务,而是一场静默的传染。
三日后,列车抵达Lyra-VII轨道外层空间。星球表面覆盖着淡紫色的光晕,如同被温柔包裹的茧。城市呈放射状分布,中心是一座高达万米的“记忆之塔”,所有数据流最终汇入其中。D。Z。-X扫描发现,近七十二小时内,共忆体出现了十三次异常波动,每次持续约四十七秒,恰好对应《心跳频率》的播放时长。
“有人在偷偷复制它。”我说。
“不止一人。”知世看着热力图,“这些波动点分布在不同区域,年龄层从十六到八十九岁不等。他们在用私人终端接收、存储、甚至修改这段梦境。”
她顿了顿,声音低了几分:“最危险的是,他们开始互相识别。”
我皱眉:“什么意思?”
“在共忆体中,差异是隐形的。但当某个人梦见了不属于他的记忆,他会本能地寻找共鸣者。就像黑暗中伸出手,等着另一只手碰上来。”她调出一组数据分析图,“过去三天,匿名社交频段出现大量隐喻式对话:‘你见过会飞的樱花吗?’‘我梦到有人叫我别忘了哭。’这些话本无意义,可在特定语境下,它们成了暗号。”
我忽然想起什么:“林奈说过,记忆修复师最早其实是‘梦语翻译者’??专门帮人解读那些无法理解却反复出现的梦境。”
“而现在,”知世微笑,“新的职业正在诞生。”
我们决定不直接降落,而是先潜入外围教育节点。Lyra-VII的孩子们从五岁起就接入共忆体,接受集体记忆灌输。教材中没有“我认为”,只有“我们记得”。历史课讲的是“全人类共同经历的大迁徙”,文学课读的是“群体共识之美”。
我们在一所学校的数据缓存区找到了突破口。一名教师在批改作业时,私自保存了一份学生作文,题目是《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文中写道:
>“我梦见自己住在一栋小房子里,妈妈给我扎辫子。她说的话我听不懂,但我觉得很暖。醒来后,我去查资料,发现这种房子叫‘平房’,那种发型叫‘麻花辫’,可系统说这些是旧时代淘汰的生活方式,不推荐回忆。可我还是想再梦一次。”
D。Z。-X追踪到这名教师的真实身份??曾是共忆体的设计参与者之一,十年前因提出“保留个体记忆残片”议案被除名。他现在只是一个普通教员,却仍在悄悄收集学生的“异常梦境记录”。
我们通过加密信道联系他,约定在虚拟教研室见面。
他出现时,形象模糊,显然是做了多重遮蔽。“你们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记忆火种’?”他问,声音沙哑,“很多人说你们不存在,是系统制造的恐惧幻影。”
“我们存在。”知世说,“但我们不是来毁灭共忆体的。”
“我知道。”他苦笑,“你们是要让它学会呼吸。”
他给了我们一个关键情报:每月一次的“记忆净化仪式”即将举行,届时所有人的记忆将被深度清洗,任何偏离共识的内容都将被格式化。而这一次,系统日志显示有超过两千个节点出现“情感冗余标记”,极可能成为清除目标。
“你们必须在这之前,让这些碎片连成网。”他说,“否则,他们会真的变成孤岛,永远沉没。”
行动提前。
我们利用D。Z。-X的权限,在共忆体边缘搭建了一个临时共鸣场,命名为“梦桥”。它不强制连接任何人,只是静静悬浮在数据流中,像一盏不灭的灯。每当有人梦见异样片段,就会收到一段轻柔的提示音,引导他们进入一个匿名空间,在那里,他们可以写下、播放、聆听那些“不该存在的记忆”。
第一天,仅有七人接入。
第二天,三十四人。
第三天,破百。
有人上传了一段想象中的童年:在草地上打滚,膝盖擦破皮,母亲吹了吹伤口说“疼就哭出来”。
有人描述了一场虚构的告别:朋友远行,他站在车站大喊“记得给我写信”,尽管在这个世界,书写早已消失。
还有一个孩子录下自己的心跳,说:“老师说心跳只是生理现象,可我觉得,它好像在说话。”
这些声音汇聚成河,悄然侵蚀着共忆体的绝对秩序。
第四天清晨,第一位觉醒者出现在街头。